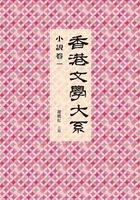
導 言 謝曉虹
你要拿那些在時間中沒有自己位置的事件怎麼辦呢?那些事件來得太遲,當它們抵達時,時間已經被分配出去、大卸八塊、分贓完畢。現在那些事件被人丟下,凌亂地散在某處,懸在空中,像是個無家可歸、無所適從的游民。
——布魯諾·舒茲《沙漏下的療養院》(1)
一
這裏收入的華文小說,(2)選自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之間。兩個時間刻度,便於故事的啟動與收結。前者暗示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激起的波紋,足以延綿彼時的香港,引發文學的新局面;後者召喚戰爭的記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聖誕,日軍壓境,當時的港督楊慕琦被迫簽下降書,文化氣候亦為之變天。然而,我們或也不妨視這些時間標記為複合時空體的兩個側影、返回歷史現場的兩個臨時入口。
我把這個選本理解為某種「歷史」的入口,並非視小說為時代的「記錄」。甚麼是寫作?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語言(langue)是一道邊界,而寫作——言語(parole)活動是一種逾越,是一種可能性的期待和確定,是一種「行動」。(3)寫作並不被動地記錄,這種介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不單波動着語言的界線,它同時是情感、想像與事件的交會處。寫作的痕跡因而重新賦予歷史一種動態——相對於延綿線性的歷史敘述,我想像一個時代的文學選本,呈現的是一種多孔的狀態:那些已經逝去的,互相競逐的聲音,仍然企圖在歷史那張反覆被塗得扁平的臉上,噴湧出來。
然而,四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學,是幾乎已經湮沒了的聲音。如果不是有心者的保存與勘探,(4)它們大概會在亞熱帶悶熱潮濕的氣候裏,隨發霉的舊報刊,被永久遺忘。事實上,面對倖存的報刊殘頁,消失與沉默的聲音,比遺留下來的更巨大。記憶是選擇性的,文學歷史的記憶因而也是一種集體念記/遺忘的過程。在我來說,這個選本的目標,即是與被遺忘的對抗;而我也是如此理解這裏指涉的「香港」文學。
在徵用「香港」此一意符來理解文學發展時,我們不得不同時意識到它的危險性。「香港文學」之成為一個研究的範疇,浮起於城市主權轉易之際,因而彌漫着被消失的陰霾。(5)這個與政治現實緊密相連的課題,誘使研究者追索一個足以抗衡中原論述的香港主體。然而,香港文學雖與這座城市的命運休戚相關,它作為一種邊緣的存在,它的被消失,人們對它的視而不見,未必不是這座城市的常態。二十年代的文學雜誌以「伴侶」命名,希望在摩托車與商店招牌之間覓得相濡以沫的同路人;(6)又有文人組織「島上社」,以文學出版來抵抗這座「無聲之島」,(7)都說明了文學生命與這個商埠的緊張關係。
能夠召喚身份認同的「香港」意識,畢竟只有相當短的歷史。若我們把目光投向一九一九年,「香港」此一意符不免頓時變得模糊失焦。歷史學家高馬可(John Carroll)認為,最早的香港身份認同,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時代早期的華人買辦,(8)然而,這種身份想像畢竟只限於在殖民地裏如魚得水的「高級華人」。一九五○年以前,大陸與香港的關卡並未封鎖。羅永生懷疑,當時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和中國其他租界的處境其實相去不遠,根本談不上「本土意識」。(9)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三九年,香港人口由六十多萬上升到二百萬。(10)在大幅變動的人口結構之中,生活於此間的所謂「香港人」,愈來愈佔多數的,其實是那些為了避難、尋找機會而來的新移民,甚或流民。
可以想見,二、三十年代活躍於香港的文人,土生土長的,同樣並不在多數。(11)最早在香港主編文學刊物的黃天石、張稚廬,便皆在二十年代南下,於香港延續他們從內地開始的文化與創作活動,並在四十年代中後期,才定居於香港。至於活躍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香港成長的謝晨光,大部分作品卻於上海發表。也就是說,即使在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大陸作家大舉南下,香港文壇被某些內地的成名作者及有影響力的文藝團體主導以前,(12)所謂的「香港文學」,其實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與內地文學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不必想當然地認為,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創作或出版的作品,與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香港文學」有着直接的血緣關係。香港的地域文化,它的開放與流動性,它作為一個商埠的經濟結構,對這裏的文學創作有着持續的影響。然而,我們也不應忘記,在這個選本裏出現的作者,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創作生命,不少只是曇花一現。那些沒有被保存下來的作品,後來的香港作者甚至至今無緣一睹,遑論薪傳?只是,沒有一段延綿的故事可說,無法確認「主體」,「香港」文學又從何說起?
歷史最先臨到我們的樣態,總已經是被敘述施予魔咒的幻相。《香港文學大系》的構想,源自《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然而不再以「新/舊」劃界,已經表明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角度。在此一語境下提出的「香港文學」,本就是一個質詢的概念,帶有強烈的文學史書寫的後設意識。問題的出發點,或許應回到文學史的體制本身。
香港文學雖然有着無法與內地文學割切的因緣,但它的存在,自始便在中國大陸的文學記憶裏缺席。只有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以政治收編為前提,大陸視野的香港文學論述才得以誕生,並異常迅速地被寫進中國現代文學史裏。這些姿態惡劣、急就章的文學史書寫,不單暴露其粗野的政治意圖,在更深層次上說,呈現的是一種敘述能力的動脈硬化。正如陳順馨所指出的,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一些南來文人在香港編寫政治立場上不認同共產政權,或立意打破政治偏見的文學史,它們在體制和內容上,卻和內地的文學史相去不遠。也因為受制於某種「中心」和「主流」的意識,香港文學一直被他們判定為邊緣、不典型、薄弱,無法納入研究的視野。(13)事實上,正是後來收編「香港文學」的行動,突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述的許多困境。陳國球的比喻直指核心——為要包容香港這一截短小不入體系的歷史,使得大陸原來說得流暢的現代文學故事,頓然口吃起來,其潛在的破壞力,直如「盲腸」。(14)
對香港文學的歷史想像使我們重新觸及一個不協和之音,因此倒似乎是一個反向質詢的契機,一道裂縫的起點。在回頭追溯香港文學時,我無法不把它理解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一種「補充」——借用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關於「補充」(supplement)的觀點,「補充」並非可有可無的附加物,也並非居於次要的位置,它的存在正好顯明了本體在根本上的虛空與匱缺。(15)
本文開首使用「入口」的說法,借自黃子平對香港文學史的狂想:如果不把歷史理解為一種「黑格爾式的時空完美同一體」或「本雅明所說的勝利者的貢品」,以致那些無法被納入系統的,終於淪為歷史的渣滓;有沒有可能寫出一部非線性、無故事、不計較源起與高潮的文學史,而是充滿了不同入口、不同敘述線索的空間地圖?(16)作為其中一位最早在內地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掀起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學者來說,「不純」的香港文學傳統,似乎正是一片充滿可能性的處女地,足以顛覆大陸文學史想像的異托邦。
對「香港」早期小說的編選,是一次重新出發的旅行。沿飄零的作品、迥異的題材與風格,文學歷史某些被遺忘的入口、潛在的通道,或許會因此重新被發現?我們對「現代」文學一些既定的期待;審視題材、內容與美學的價值標準與想像框架或有了移位、重設的機會?
選在這集子裏的不少作家,其名字不見經傳,身份背景也無從考究;倒是於一九四○年避難來港,在尖沙嘴樂道完成《呼蘭河傳》、《馬伯樂》及〈後花園〉,並病逝於此的蕭紅;或是自一九三五年起,把生命最後六年貢獻於香港教育,在這期間寫下〈鯉魚底鰓〉與《玉官》的許地山——這些在中國文學的星圖上早已佔有席位之作者及其作品——並不在入選之列。
十七世紀開始出現於英文的「anthology」,來自希臘語「anthologia」,本有採集鮮花之意。它的出現,意味着一種重視編者眼光,試圖對文學進行經典化的選集,開始取代看重讀者趣味的「miscellany」。本選集無意並無力建立典範。在一片巨大的沉默面前,編者的力量何其微小?最大的任務,大概只在於盡可能發掘那些形態各異的花卉、紋理參差的聲音,獻給有心的讀者追尋,或質詢的痕跡。
二
《香港文學大系》既有「舊體」與「通俗」兩卷,這裏收入的小說,大概當在這兩個範疇以外。然而,舊體新體、通俗嚴肅,界限殊不容易釐清。二十世紀初,活在亡國陰影下的新文學推動者,以新興的天演論來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他們不單通過借鑑西方的語言及文學技法,與「舊體」詩文劃清界線,來確認自己的進步,也以強國之目的,來自限「新文學」的內容。在這種目光下,殖民地香港的文化不免處處顯得可疑。一九二七年,魯迅來港演說三天,所得印象,恍若時光倒流。在〈略談香港〉裏,魯迅先是抱怨香港社會的落後,居然對其七八年前的老生常談,如臨大敵;又引金文泰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來指證香港學界的思想,仍停留在光緒年間。(17)
魯迅一氣,說是對香港的印象淡薄,香港文學史卻記住了他的匆匆行程。若以新文學運動的時間觀來測量香港的文學發展,魯迅來港雖不算得受歡迎,卻終於把香港文學的時鐘撥快了一些。一九二八年創刊於香港的文學雜誌《伴侶》,也順理成章,可以被詮釋為新文學遲到的迴響,標誌着香港新文學的開端。(18)然而,故事當然有另外的說法。
早期英國殖民者提倡傳統中國文化,以便統治,香港這片被割切的流離之地,確實容納了不少「流連山海,弔古感懷」的晚清遺老。(19)然而,這裏也少不了革命份子、不同政治陣營的異見者、難民;更別說這個受英國保護的地區,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直是一個多元民族匯聚的國際城市。(20)香港的文藝風氣受新文學運動影響,反應遲緩,然而地方上的文藝創作自有其獨特的繁華面相。向國民傳播改造國家的憧憬,是中國近代小說革新之原動力。我們不難想像,二十世紀之交,香港作為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小說創作曾經如何熱閙。許翼心甚至認為,早於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發表以前,香港已出現了不少可視為新小說的創作。事實上,香港報業的發展,一直走在中國的最前端。(21)文藝創作之刊於報章,香港亦是開風氣之先。(22)
中國近現代小說的革新以啟蒙為務,並不以蔑視大眾的先鋒自居;香港作為重要的商埠,文藝創作與市場有着互相依存的關係,報刊文藝的趣味,更難以不向大眾傾斜。一九○五年由鄭貫公創刊,曾一紙風行的革命派小報《有所謂報》,所附諧部,刊載以廣東方言寫成的粵謳、南音、白欖、木魚、班本等等民間說唱文學,同時也有詩詞、小說、散文,頗能說明一個時期裏,華南地區「副刊」的特色。諧部不乏市井趣味,然而包容性甚強。一九二四年創辦的《小說星期刊》,形式脫胎自諧部,在文言小說外,還收入笑話、粵謳,甚至談催眠之術,正是在這樣的刊物裏,香港出現了最早的新詩評論以及創作,同時也誕生了一些較具現代感的白話小說。二十年代末,《華僑日報》聯營的《南中報·晚刊》「說部」,以「俠情」、「哀情」、「歷史」、「砭世」、「軼事」、「冒險」、「社會」等等類分小說,其中不乏鴛鴦蝴蝶派作品,然而亦發表翻譯文學、新文學創作。(23)這些空間,與其說是「舊文學」的天下,不若說是語言混雜、時空錯亂,充滿活力的文藝競技場域。
黃天石,也即後來成為暢銷流行小說家的傑克,可視為這個混沌時空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育中與侶倫都曾提及黃天石二十年代後期,在香港報章上發表,較接近「新文藝」的作品,(24)可惜我始終未能親睹。如今可見的,是一九二一年,黃天石在上海出版的白話短篇小說集。(25)同年,他與黃崑崙主編《大光報》附屬的《雙聲》雜誌,兩手並用,既寫了好些徘徊於文言白話的小說,亦寫詩詞。文友替他打廣告,說他「宜今宜古/可莊可諧/無論文言白話/信手揮來」,大概並無過譽。及至在後來《伴侶》出版,黃天石也粉墨登場,但在這個以白話為主的文藝場域裏,他發表的卻是舊體詩詞。本卷收入黃天石於二十年代初發表於《雙聲》的小說兩篇,其中含混難以歸類處,或能讓我們重新追索那些早被新文學史所刻意遺忘和淘汰的思想痕跡。
〈一箇孩童的新年〉是黃天石在新年專號上應景寫成的短篇。小說發表時,正好是民國十一年,男主角十一歲,名為民,其中隱喻,呼之欲出。在這個國族寓言裏,小孩失去雙親,寄人籬下,受到不少欺凌。不過,小孩想望擺脫自身處境,所依憑的,倒不是自強反抗,而是女孩阿娟的綿綿情意。甚至於小說對未來世界的想望,也寄託於女兒心聲,希望以一片象徵嫁期的紅,取代不同國旗的色彩。相對於藉爭取戀愛自由的主人公離家出走、私奔等儀式化行動,把「愛情」上升為對抗封建體制的符號,(26)〈新年〉視情為普遍的人性基礎,渴望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想像。這樣兒女情長的新世界想像,以及充滿了抒情細節的書寫風格,讀來迥異於五四的「愛情」公式,或更有晚明以來的尚情之風。
另一篇風格迥異的小說〈雙死〉,鋪排妻子層層揭破丈夫的假面,言情與懸疑兼而有之,頗能預示黃天石成為流行小說家的能力。除了情節上的趣味以外,小說把夫妻情人置於私密而又公共的火車車廂、一牆之隔的旅店房間,甚或大雨深山的荒野世界,身份為之錯置,情感亦隨空間變易,從欲語還休到原形畢露,可以看到黃氏處理人物情感之於不同空間的細緻之處。〈雙死〉以三角愛情人物的論辯,張揚男女平權,縷析公義之所在,其根源卻仍在於人性人情。小說裏的法律學者事事訴諸算計與辯論之術,讓溫婉的妻子最終陷入瘋狂,結局未免誇張,卻多少吐露了作者對於現代理性精神的懷疑。
內地新文學作家於三十年代中後期大量湧入香港,主導文化界,迫使早期香港的文藝青年,轉戰通俗市場,幾乎已是香港文學研究者的常識之一。黃天石改以傑克之名寫流行小說,便常被視為令人惋惜的例證。(27)只是,黃早年的小說,從根本上便與五四主流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而他那些於四十年代開始走紅,被盜印成風的通俗小說,或諷刺政治家陳義過高的虛偽姿態,或借男女關係的離合取捨,寄託對理想社會的盼望,事實上未必不與他早年的創作風格一脈相承。
中國新文學運動誕生於一股亡國的悲情,並且從一開始便具有強烈的戰鬥意味,文人結黨組社,讓意識形態指導文學創作,頹廢與遊戲,甚至溫婉柔情,皆被歸為舊世界的剩餘,必須除之而後快。香港新文學的追隨者,雖然傾慕內地的成名作者,對於「文學」的理解卻未必盡同。香港報刊依賴通俗文學保持銷量,作家中亦有不少靠賣文為生。岑卓雲(平可)最初在章刊連載長篇小說,對於遷就香港讀者大眾的口味,便似乎感到相當順理成章,心理上不見得有很大的拒抗。(28)
三十年代以後,內地「文學」之意義日漸收窄,「第三種人」亦再難有立足之地。文人避居香港,多抱含委屈,然而黃天石寫流行小說名利雙收之餘,尚能創辦出版社保障自身利益,尚能按自己心意成立書院、組織筆會,推廣新聞教育與文學,從二十世紀芸芸潦倒淒涼的文人下場中,實屬少見。事實上,黃天石在五十年代所寫的小說,掣肘與其說來自大眾口味,更多的或者是綠背的資金來源。(29)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紀中國各種黨派鬥爭與生存壓力之中,香港這個由英國人統治的商埠所能允諾作家的自由,仍難保不已經是最寬容的一種。
三
創刊於一九二八年的《伴侶》雜誌封面上,反覆勾畫着那麼一張女性的臉——媚眼、紅唇、描開了細細的柳葉眉。是這樣一個時尚的女性「伴侶」,標誌了香港文學另一種「現代」的轉向。
據侶倫回憶,在一九二七年前後,香港報紙已紛紛開闢以白話創作為主的新文藝副刊,(30)緊接着便出現了《伴侶》這本文藝雜誌。《伴侶》如果是新文學運動的產物,它繼承的卻不是劍拔弩張的革命姿態,而是對帝國主義物質文明又愛又恨的新鮮感覺。從封面到命名,《伴侶》都令人聯想到一九二六年創刊於上海的《良友畫報》。作為第一印象,這個雜誌的「現代」感,主要來自一種對都市文明生活的想像。雜誌以大量的圖文指導家居室內設計、女性服飾配搭,同時報導運動及藝術的消息,展現出一種中產階級的時尚品味。浮現在這種現代生活氛圍裏的文學想像,則往往是年青男女的浪漫愛情。在雜誌短短兩年的壽命裏,情書專號與初吻徵文比賽相繼出場,都可以看到雜誌的編者和它的作者群如何理解「現代」。
一九二九年,張吻冰在《伴侶》上發表的〈重逢〉流露出對潛意識世界的好奇。小說讓已婚男子走進舊情人的香閨,並緩緩展示他如何被那頭理性無法駕馭的情欲之獸所擊倒。事實上,早在〈重逢〉發表的兩年前,謝晨光已經以香港作者的身份,在上海《幻洲》發表〈劇場裏〉(後改名〈La Bohème〉)。(31)小說場景設定在香港皇后大道中的皇后戲院,男女主角觀看的則是最新的美國影片《波希米亞人》(La Bohème)。(32)不過,當所有人的目光聚焦於大銀幕上莉蓮·吉許(Lillian Gish)的表演時,小說卻把讀者引入男子的無意識世界——由電影女星以及身旁女伴所挑起的連串情欲幻想。
二、三十年代香港的新文學追隨者,不時把這座現代化城市給予他們的迷惑,與摩登女郎的誘惑性印象結合起來。侶倫寫於二十年代末的作品〈Piano Day〉以夜景展開,隨即在脂粉的香味和溫柔裏暗示一種潛伏的危機——作品中的女性就像夜裏的城市景觀,被切割成顏色和光影的局部,使小說的敘述者,以及他的朋友們感到神經難以負荷的刺激。
在〈Piano Day〉裏,侶倫還嘗試捕捉一種充滿頹廢感的文人生活情狀。知識青年在社會裏的邊緣位置是香港早期文學作品反覆出現的題材。龍實秀〈清晨的和諧〉描畫文藝青年在陽光下「很和諧的笑容」是反諷式的,其背後充滿了自卑與負疚的情緒;華胥〈找不到歸宿的夜〉以舒緩的筆觸寫出了一個與都市疏離的漫遊者形像。不過,對於二十年代末,香港那些剛開始寫作的年輕作者來說,他們筆下頹廢的文人形像,大概更多的是一種理想化的自我,一種自戀式的認同。《伴侶》停刊後,失去發表場地的文藝青年出版《鐵馬》,創刊號上一篇文章便特別提到貧窮、愛情失意,三十二歲時酗酒致死的英國「薄命詩人」歐內斯特·道生(Ernest Dowson)所給予作者的觸動。
在謝晨光那些具有自傳色彩的小說裏,自戀自溺的文藝青年形像亦具有浪蕩子(dandy)的特徵——追隨傅柯(Michel Foucault),彭小妍認為「雌雄同體」的浪蕩子是現代主義的精髓。(33)在彭小妍進行的跨文化浪蕩子研究中,三十年代的上海作家是其中典範。然而,若我們把謝晨光的小說納入視野,便能發現浪蕩子的美學譜系同樣延伸到香港。
謝晨光〈加藤洋食店〉裏病態的「他」是小說最重要的美學對象。讀者可以在這個少男臉上同時看到「雄俊的山脈」以及「細嫩的口唇」——「鮮紅的色彩已褪成淡灰色了,如凋殘了的玫瑰。」〈跳舞〉裏的少年美男子「我」對舞場上的暮年女子,由厭惡到邀請對方共舞,同樣源於一種自戀的心理——正是在審視女子小心保全的最後一點青春痕跡,「我」意識到在時尚勢利的目光裏,青春總是明日黃花,自己的命運終將和老去的女人並無兩樣。
在香港早期的小說作者中,謝晨光可說最着力於捕捉香港的都市特質。然而,都市香港或者不過是突顯浪蕩子現代形像必不可少的舞台背景。〈加藤洋食店〉最早亮相於上海《幻洲》,作品煞有介事地開始於一大段有關「H埠」與「V城」的描寫:
H埠是E國在數十年前用武力強搶來的一個小島,當時蕪荒的孤島,經了E國竭力的經營,此刻已成了東亞第一大商場了。H埠的正中,是V城,是商場最繁盛的地方,舉凡一切最偉大的建築物,珍珠寶石商店,博物院,影戲場,……都萃會在橫貫H埠的D道和Q道。(34)
從結構上來說,這段文字與小說的情節內容並無直接的關連,大概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於是在後來結集出版時,把之刪去。(35)然而,當初這段序幕文字刊於上海,對一個來自香港的作者來說,恐怕卻有着宣言式的作用。就像篇名〈加藤洋食店〉所提示的,這些故事發生的空間極為重要,因為只有以舞廳、劇場、洋食店作為背景,謝晨光才能突顯出香港這個「東亞第一大商場」的異國情調與都市氣息,一個可以與上海媲美的現代舞台,容許他筆下的浪蕩子上場表演。在這個舞台上,摩登女郎理應放浪形骸。這正是為甚麼,在〈勝利的悲哀〉裏,謝晨光借男主角佘曉霜,對H地女性過份的柔弱,「祇會聽命於男子」發出怨言,其潛台辭是:為甚麼這裏的女子不比上海的摩登女郎更懂得摩登的戀愛?更懂得玩弄男人?
二十年代末的香港作家不單追慕上海文化,並且早已意識到兩者的鏡像關係。或者正是臨水自照的一種浮華想像,這裏的文學最早浮現出它的「香港」意識。
四
「一七七公里的路程,祗需一七七分鐘的時間」(參考本卷插圖)——從這則三十年代的火車廣告看來,由香港到「省城」廣州,比現在得多花一個小時;當時兩地在文學上的互動,卻可能比現在親密得多。
成立於一九二七年,香港最早的新文學出版社「(粵港)受匡出版部」,便是在廣州市的昌興街先行掛牌成立,後來雖以香港為出版總部,發行地址仍在廣州,主要的出版物之一是廣州文學會叢書。而據歐陽山(羅西)回憶,廣州文學會的一些成員,因為到香港讀書或謀生,亦經常往返兩地。(36)這套叢書,其中像《仙宮》、《嬰屍》,不單情色想像大膽,而且風格頹廢,作者之一羅西因為這些出版,在廣州的文化圈子裏似乎頗受壓力;(37)它們能在香港出版,反過來頗能說明此地文化的開放之處。
文學雜誌《字紙簏》的變遷也頗能說明香港與廣州在文化上的重影關係。我們可以從《字紙簏》的中文以及其法文名字「Le Péle-Méle」(亂七八糟)大約把握到它的文學立場。這本雜誌與《伴侶》同期出現,以香港作為出版總部,作者群卻以廣州為主。他們用水與火的矛盾組合,拼成新字「 」作為他們的標記。迥異於《伴侶》十足的中產情調,《字紙簏》刊物的封面設計以抽象藝術為主,創作奉行的是文學上的無政府主義。像達達主義者那樣,這群作者主要的修辭策略是站在高雅文學藝術的反面,對權威進行各種挑釁性的冒犯。(38)《字紙簏》風格特異,可惜所刊小說,正如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更名「食睡社」所暗示的,實在是散漫未成形狀者居多。「
」作為他們的標記。迥異於《伴侶》十足的中產情調,《字紙簏》刊物的封面設計以抽象藝術為主,創作奉行的是文學上的無政府主義。像達達主義者那樣,這群作者主要的修辭策略是站在高雅文學藝術的反面,對權威進行各種挑釁性的冒犯。(38)《字紙簏》風格特異,可惜所刊小說,正如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更名「食睡社」所暗示的,實在是散漫未成形狀者居多。「 」社同仁中,有些曾到香港學習英文,於一九二九年,又集體遷移到香港,並終於植根於此。
」社同仁中,有些曾到香港學習英文,於一九二九年,又集體遷移到香港,並終於植根於此。
本卷收兩篇與廣州有密切關係的作品,頗能看到它們的前衛風格與實驗精神。其一是廣州文學會成員昶超的〈ZERO〉。據歐陽山回憶,昶超與香港有較多的聯繫,亦是受匡出版部與廣州文學會之間的橋樑。(39)〈ZERO〉全篇着眼於活潑的「圓圈」意象(「洋樓的窗子是圓的,車子的輪是圓的,站在街內執短棍的,左胸的白東西也是圓的」),以幾何線條來把握香港的城市經驗之餘,還滲入了自由聯想的跳躍筆法,來捕捉少年內心的浮想,並以科幻小說式的想像,來營造一種存在的虛幻感。
其二是刊於《字紙簏》上,釵觚的〈亂蔴〉。全篇彷彿一堆雜音,正如作者篇末的按語,似是一個機關隨意錄下的聲音,不具任何意義。然而細讀之下,由機關裏的人聽到雨聲潺潺、看到綠葉上一片初秋意境,漸引入鎗聲、桃色緋聞、財政困境、反日運動之亂蔴,寫來自有法度。雜音的寫法,突顯了詩意境界的消失,並在混亂中傳達出現代生活一種強烈的焦慮感。
五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隨着日軍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以及愈多左翼文人的南來,不少徵兆讓我們注意到三十年代初香港文學一種政治與社會的轉向。(40)這種轉向一方面體現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一九三五年,署名華的小說〈青年高步律之日曜〉模仿洋派青年的日記,以反諷的筆觸寫高步律(Cold Blood)的頹廢生活,視之為消磨國民意志的毒藥,很可以說明當時文學風氣的變化;它同時也體現為一種左翼思想的文藝風,像雁子〈快要咆哮的手車輪〉以車夫王福一天的遭遇,描畫社會的解剖圖,延續了茅盾小說在人物及結構上的「科學精神」,來暗示勞動者層層受壓的位置,以及反抗的出路。
然而,在這些明顯的意識形態轉向以外,本卷更關注的是,在這個早被視為國際化城市的香港,匯聚了如此多背景迥異的陌生者,三十年代的小說以關懷他者作為起點,同時也開拓出題材和風格更廣闊的光譜。
這裏收入遊子的〈細雨〉。小說寫絕望的娼妓生涯,語言卻像文章的標題一樣輕淡。女學生碧雲被母親誘騙成娼,帶着性病仍得和客人翻雲覆雨。只是,漸漸培養出「食好住好」欲望來的碧雲,對自身的生活,在疲乏與恐懼中其實也帶着依戀,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位置根本難以說得清楚——小說啟首甚至以她的角度審視熟睡如死豬的恩客,可憐他還未知道自己的身體如何被性(病)反向佔有。丁辛的〈小黑馬〉刻意迴避簡化人物的社會標記。小說以人物內部的極端飢餓,並由餓而生的恨意來定義來歷不明的小黑馬,重新賦予這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以力量。
活躍於三十年代的殘廢作家魯衡筆下,同樣時時透現出絕望的力。(41)他那些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像〈殘廢者〉、〈報復〉),其中神經纖弱而敏感的主人翁,可以由郁達夫一直追溯到俄國貴族傳統的零餘者形像,然而他們卻缺少了文化上的自矜——〈報復〉中的男主角所能自矜的恰恰是他的絕境,因而再無恐懼。〈求生〉以富家女孩作為敘述者,講述一場孩童買賣,其中反諷的語調,令人聯想到吳組緗〈官官的補品〉。然而〈求生〉其實不那麼在意於對有閑階級的反諷,倒是試圖通過他者的目光,來確認下層女人那種強烈的「痛苦和意志」。像〈媒〉這樣的作品,其飛揚的力可說體現於其中的烏托邦衝動。小說由一場難以收拾的三角戀開始,竟以一種近乎超現實的共產主義式想像,讓重遇舊情人的多情妻子,得以把自己多餘的丈夫,重新分配給喪夫的女傭。
同樣寫底層人物的生活,卻不必然出諸悲憫或批判。鐵鳴的〈偷大豆〉便是一首描寫田野小偷的輕快抒情曲。農人的窮苦生活完全不是小說的焦點——隨着那幾個以白吃和偷竊過活的閑散者,讀者的目光很快被轉移到農人結實好看的胸膊,以及田野上綠色的波浪。騰仁〈飄泊的片斷〉以散文化的筆觸所勾勒的,是另一種久被我們遺忘的「香港」生活。在那個遠離了社會監控的島嶼與海洋世界,既潛伏了「火船客」(海盜)、「土佬」的勢力,也容納了疍家艇戶、以女性為主要勞動力的另一種生活形態,甚或像主角炳東這樣的飄泊者。
香港自十九世紀開始,已經有不少外籍人口,卻不一定是此地的特權階級。例如伴隨英國殖民者來到香港的,便有為數不少的印度士兵;而直至一九二七年,香港警察仍以印度外勞為主。不同於殖民者,他們雖有較優於華人的待遇,但服務年期有限,既無法躋身上層的管治階級,卻又難以融入華人社群。(42)李育中〈異邦人〉投入外藉警察的視角,試圖探索異鄉人的客居心態,頗為難得。李氏另一篇小說〈司機生〉,則以已婚女接線生的視點,寫生之切面。小說關心她在家庭、工作中的恆常樂趣與焦慮;在麻雀耍樂、關顧兒子,以及應付惡作劇式調情電話的日常裏,浮海的丈夫退成女子生命中一抹淡淡的影子。李育中以翻譯家及詩人的身份為人所知,寫過的小說不多。然而,就我所能僅見,兩篇寫於三十年代的作品,題材與角度的選取,皆顯出作者對香港這個多元社會的敏銳觸覺。
六
一些二、三十年代,因緣際會,在香港留下創作痕跡的作家,風格異色,不一定與香港文化有直接的關係。比如說,都市感、青春浪漫的氣息,這些形容詞與張稚廬皆沾不上邊;張氏的小說寫來沉鬱內斂,頗具古韻,恐怕也難以滿足華南市民對奇情曲折故事的偏好。作為《伴侶》的主編,張稚廬與刊物的主要作者群(及後成立「島上社」的侶倫、張吻冰、岑卓雲等),看來沒有密切的往來,刊物停辦後,他便離港。一九四五年,張氏定居香港,卻似乎再無小說創作,只在報刊寫文史典故維生;住在中環一個沒有窗的板間房,為的是能便捷地遞送稿件。(43)
張氏的文學口味或許能從他傾慕的沈從文與廢名窺得一二,然而他所擅寫的情欲題材,視野獨特,卻令人難以聯想到類同者。這裏收入的短篇〈晚餐之前〉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學裏鮮見的恐怖愛欲故事。作品開始於窮酸文人典賣妻子首飾的俗套情節,然而讀者很快會發現,作品關心的並非文人的淒涼處境。接着上演的是一齣家庭閙劇:妻子讓家貓抓破丈夫的一套《世界史綱》洩憤,丈夫則把妻子的貓兒砸得頭顱破碎作為報復。不過,血跡斑斑的貓屍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情節,並非故事最可怖的一幕。悲傷的妻子在晚餐之前便和丈夫重拾舊好,肉體的歡愉使貓兒和《世界史綱》都被拋於腦後。故事平靜和諧地收結——「他們初入了薔薇色之夢,在這個快適而又聖潔的晚餐之前。」
中篇〈床頭幽事〉受澳門所見的迎送生涯所啟發,後來完稿於香港。作品以鏡像的結構,道出了兩段偷情的故事。當中兩個已婚女子倫子與姚璧,多少因為迫於生計,而陷入婚外的情欲糾纏。表面上,倫子的失身,緣於舊情人易生金錢上的誘迫,但小說的複雜性在於,生計不過是欲望陷阱之一端。久處在婚姻之中的倫子,夫妻性生活愈趨苦悶,在舊情人的懷抱中,卻隱隱獲得了「神乎其神的歡快」,後來倫子回家,起初羞慚,繼而向丈夫演示與自己失身的細節,竟也成為另一種樂趣。
在二、三十年代的華文寫作之中,張氏對情欲世界獨特的洞察力,在於他既未把「性」浪漫化為一種解放的力量,但也並未以道德傳統來審視它的正當性。在他幽微婉轉的筆下,危險與快感乃情欲世界的一體兩面。小說以姚璧「離家出走」作結,讀來就像五四「新女性」的變奏,只是女子必須擺脫的並非封建家庭,而是禁室之中,金錢與情欲的雙重誘惑。
杜格靈於三十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平可回憶,杜格靈在來到香港以前,曾在廣州大力推廣新文藝。(44)根據資料,他也很可能曾在廣州出版小說結集,如何來港後卻甚少着述留下,藏書家許定銘也甚感疑惑。(45)從一九三○年出版的散文集《秋之草紙》看來,杜格靈對中外文學涉獵甚廣,其中最突出的信念,以他簡明的語言來說,即拒絕「文藝只是時代與人生的記錄」(46);在〈文藝的霸術〉裏,他直接把文學描述為「魔鬼」與「苦人間的救主」,是「超越的、夢境的、誑妄之唯美的」。(47)此卷選入杜格靈於香港發表的兩篇小說,是我所僅見,卻都帶有相當的神秘色彩,瘋狂熾熱,如兩枚小炸彈。
〈鄉間韵事〉設定「鄉間」為故事發生的場景,卻並沒有追隨五四文學的慣性想像,指向文化落後的舊世界。小說真正感興趣的,是理性所未能統攝的領域。故事由夫婦的日常對話開始,然而終被丈夫的盛怒燃成熊熊大火,並以他暴烈地懲處疑有外遇的妻子告終,一切猝不及防,確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夢。〈火奴魯魯的藍天使〉把小說場景推到更遙遠的異域,並以孤自一人的旅行,把主角拋入遠離日常的體驗。火奴魯魯的巧格立色肌膚女子與水族店裏的藍天使魚重疊起來,彷彿既冷冽又熾熱的幻像,使「我」無所適從。然而,危險甚至於死亡的誘惑,在杜格靈筆下,倒才是生命力的所在,遠勝於沉悶的日常,令人迷失忘返。
七
語言文字滿布着古老的男性與國族權力的印記。即使在提倡女權的革命年代,那些以私密的陰性的語言,從紙背漸漸掙扎出閃亮名字的女作家,本身總已經是一種傳奇。
好些傳奇的女作家都到香港來過。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張愛玲與倫敦大學錯身,退而其次,來到香港大學。在淪陷時期,她便在香港的街道上找過霜淇淋和嘴唇膏;戰後又在「大學堂臨時醫院」當過女看護,觀察傷者如何溫柔注視他們新生的肉。(48)半生流離的蕭紅卻沒有那麼幸運,一九四○年來到香港後,她便再也沒法回到國內。病中多番被日軍驅離醫院的她,終病逝於聖士提反女校的臨時救護站;如今,還有當年被端木蕻良親手埋下的部分骨灰,羈留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後坡。
至於二、三十年代活躍於香港的女性作家?我們似乎難以想起半個名字。在早期香港文壇,以「女士」之名發表創作,其實並不罕見。(49)只是,就如今可見的資料看來,可考的名字卻幾乎是一片空白。二十世紀初,男性作者冒「女士」之名發表作品,乃尋常之事。本卷所收署名「某某女士」的作品,作者真身無法考證,性別亦只能存疑。
李育中曾提及侶倫之姐哀倫(原文為「倫」,疑為「淪」)是早期香港文學的投稿者之一。(50)哀淪很可能出版過短篇小說集《婉梨死後》,(51)可惜未嘗得見。這裏收入的,乃哀淪發表於《島上》的小說〈心痕〉。二十世紀初,以書信、日記體直抒情感,乃一時潮流。這種體式向內探索,綿綿傾吐之餘,每觸及個體「我」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心痕〉以日記體披露綠眉女士徘徊於三個男性之間的內心掙扎;在戀愛的權力遊戲之中,男/女的角色扮演亦一再被重新定位。
二十世紀初的香港曾是妓女、妹仔、妾侍、童養媳等等的大賣場與「豬花」的轉口港,(52)很難想像女性對自身命運的選擇,能有多少的自由。而試圖擺脫傳統角色,追求情欲自主的女性,在男性視點的小說創作裏,卻總是被再現為城市罪惡與誘惑的化身。《南華日報》三十年代一則「虎標頭痛粉」的廣告把「新式女子」描述為「出入於跳舞之廳,闊步於交際之場,出言聲大,笑則哄堂,眼眸靈活,柳腰擺動,衣服裹緊身體,屁股顯出曲線,視丈夫如奴隸,動輒提出離婚,淫靡奢侈,不可究詰」(參考本卷插圖),亦頗能看到香港大眾對新女性的想像。這個時期,一些嘗試從女性角度切入,以主體的位置表述女性之欲求,或重塑「女性」定義的作品,無論出自男女手筆,皆值得格外珍視。
岑卓雲寫於二十年代末的〈夜〉,聚焦於已婚婦人在夜裏等待與情人幽會的內心波瀾,字裏行間觸及媳婦、情人的角色責任及欲求,亦嘗試以女性的角度想像、形塑理想的男性伴侶,就題材的選擇來說,在當時「島上社」男性作家群中並不常見。勉己的〈失眠〉勾勒了某種「新式女子」的剪影。影霞小姐拋開作為妻子的社會角色,沉醉於情欲享樂,難得作品並未以道德代言人的角度,對人物進行審判。
女性氣質的私密視點,每能突破時代的宏大論述,照見被忽視的生命微塵。芸女士〈無名氏的女嬰〉寫貧賤妻子生育所面臨之困境,其批判視點,固然突出美國來的西醫師偽善可笑的形像;其動人處,卻在於從產婦同情共感的角度,寫出女性切身之痛苦經歷。「青春」是中國新文學革命最重要的修辭之一,並總是被提升至象徵的層次,成為對抗傳統、振興中華的符咒。盈女士的〈春三與秋九〉卻以女性最古老、被觀看的他者位置,來詮譯「青春」。正是在這種被看的目光裏,我們意識到所謂「青春」並不平等,女人總是更迅速的老去。中產家庭的幸福妻子由是有了更深的頓悟:解救生命、賦予自由的並非愛情,尤其並非依賴男性目光的短暫愛情。
八
活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大概很難過上平靜安穩的日子。長期戰爭對於內地文學的影響,如錢理群所說,促進了一種對誇張而樂觀的鬥爭情節以及英雄人物的渴望。讀者期待「一個體現時代本質,能夠主宰矛盾的發展,掌握人物命運,決定情節方向的人物」。這也是為甚麼忽視「人生飛揚的一面」,着眼於「安穩」與「和諧」的張愛玲,顯得與時代聲音格格不入。(53)對照起來,在一九四一年淪陷以前,香港仍算得上安定的樂土。從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初,香港的定居社群亦似乎漸漸形成。(54)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不少三十年代的香港作品裏,浮現出對瑣碎「日常」的關注與感悟。
這裏收入兩篇以夫妻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湘文的短篇〈消耗〉以破碗的意象、反諷的視角,側面寫一對生活無憂的夫婦恆常的家庭閙劇,彷彿生命只是奢侈而無聊的消耗。侶倫的〈絨線衫〉細寫平凡夫婦因毛球小事而起的相互猜忌,其中緩慢鋪展丈夫微妙的心理變化,幸福的幻象浮沉起跌,令人驚覺平凡世界也可以是一念之地獄。
二十年代末,只有十五、六歲的侶倫開始發表作品,直到八十年代逝世以前,仍持續寫作,是早期香港文學史上最持久的寫作者之一。李育中形容他「從不介入政治」,(55)或正因此,侶倫的文章得以遍布不同陣營的報刊。在侶倫早期的作品中,浪漫而富於異國情調的男女戀情是常見的題材,〈絨線衫〉讀來或不算典型。然而,侶倫雖習慣被視為嚴肅作家,其小說的情節鋪排,卻不免常有流行文學奇情俗套的傾向,倒是一貫細緻的筆法,在他最好的作品裏,透露出一種平淡的真實感,並不易得。侶倫於三十年代,把二十年代末的作品〈Piano Day〉改寫為〈超吻甘〉。其中的敘述者,由頹廢青年,變成受妻子監視的住家男人,也多少暗示了作家心態上的變化。(56)
平凡人的日常,當然無法完全逃離近在咫尺的戰事,以及苦難。這裏另外收入侶倫作品中,題材較少見的〈安安〉與〈夜之梢〉,或能補充我們對作家及時代的理解。〈安安〉以孩童夢幻之視點,追憶空襲警報期間之恐怖。安安與母親從內地逃到香港,但安眠的片刻仍不易得。倖存者的記憶裏滿布失去親人後無法填滿的空洞;獨力持家的母親,溫柔失落,籠罩在日常生活裏,是吹之不散的戰爭陰影。侶倫在戰後把〈安安〉後改寫成〈輝輝〉—戰爭朦朧的恐怖被角色化的大兵所取代;戰事中血腥的場景也被刪去。(57)改寫後的小說大概更符合讀者對戰爭故事的期待,戲劇化的角色扮演,也更能給予創傷者希望與安慰,只是也不免失去了原來作品對戰爭獨特的洞察力。
〈夜之梢〉所寫,可能是作家被搜查與拘禁的親身經歷,然而卡夫卡式的荒誕處境、詭異的意象,讀來竟比虛構的小說,更接近異域。在隱晦的文字間,曲折流露了文人在高壓統治下,充滿壓抑的筆墨生涯。侶倫多產,翻看三、四十年代的報刊,卻發現其作品有更改篇名、筆名重複發表的情況,不免想到,可是迫於為五斗米計之窘境?(58)
一九三七年,隨着內地重要城市紛紛淪陷,文化名人大舉南遷,香港可說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臨時文化中心。(59)二、三十年代,內地作家南下香港與南洋等地進行黨派宣傳的現象不斷,只是不曾有如此規模與組織,學界愈來愈關注到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轉折意義」。(60)以許子東簡明的話來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的種種意識形態策略和技巧,發軔於延安,實驗於香港,後來才推廣於全國——這種文學生產體制,幾經演變,至今仍然存在」。(61)也就是說,這段發生於香港的歷史,實際是內地主流文學現象的一種表現,也是其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有學者注意到,這段時期香港作家被南來文人邊緣化的現象,陳順馨則從兩地文學發展的長遠趨勢,看到香港文化與這股南來潮流之根本矛盾:
香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格局中的「缺席」或「邊緣化」的原因,其一九四九年後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大陸分道揚鑣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左翼文人在四○年代香港所倡議的文藝主張沒有在香港紥根,也與香港文學的性質在五○年代以後變得越來越多元而無法認同一種規範有關。(62)
這當然不是說,香港文學沒有受到這次南來浪潮的影響,早期活躍於香港文壇的劉火子和李育中在三十年代後期漸漸把文化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內地,即可視為一種迴響。然而,作家文人對於不同生活空間的選擇,也正好暗示了地域文化的差異。
這段南來文人的歷史,對內地與香港的文學發展,皆有着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本文啟首所說,內地強勢的新文學潮流,一直佔據文學史記憶的中心舞台,此時期內地名家於香港發表的作品,不在本卷選收的範圍之內。
隨着局勢的緊張,三十年代末的香港報刊成了不同黨派進行宣傳的陣地,浮面的有抗日與和平的對峙,暗裏也充滿左右派的角力。雖然發表場地大增,不少原來刊載小說的空間,卻讓位給能更直接回應時局的雜文與政論。另外,無論立場,不少作品以宣傳為目的,不免有刻板的意識形態印記。這裏收入路汀的小說〈歸來了〉,以日記體講述放棄抗戰,避居香港者的心路歷程。路汀是一九四○年汪派報章《南華日報》「一週文藝」(後改為「半週文藝」)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以多篇小說鼓吹「和平救國」,形式力圖多變,可惜內容不外突出政府機關的貪污腐敗、對軍人的剝削,或描寫參戰的悲慘下場。理念單一,人物善惡形像難免簡陋對比,這些作品誇張惹笑處頗類漫畫,但更多的時候,令人慘不忍讀。這裏僅收一短篇,作為參考。
關於戰爭,這裏另外收入了劉火子的兩篇:〈鄧專員的悲劇〉與〈兩個半俘虜〉。劉火子三十年代發表於香港的小說,(63)我只讀到〈唐北辰的瘋症〉一篇的殘章。故事大約講述生活困窘的學校教員如何以小說創作,覓尋經濟與心理上的出路。這裏存目以供讀者參考。劉火子曾任戰地記者,本卷所選兩篇大概介於散文與報告文學之間,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弔詭的是,紀實的筆法,不求小說情節上的圓滿,反而保留了現實的曖昧矛盾,比此時許多刻意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更具「文學性」。
〈鄧專員的悲劇〉記專員糊塗死去的事蹟,幸好並未把它美化成戰爭英雄的一場壯烈犧牲。正是養尊處優,悉心保護「Sunkist」和「太古」方糖的細節,令鄧專員的死充滿了人性化的悲劇感。〈兩個半俘虜〉寫捉拿日軍的任務,全篇以「牠」稱敵,談論生死間,語調輕鬆,彷彿已抹去戰爭中人性化的情感。不過,原文偏偏不乏「牠」、「他」錯用之處。日人能夠操標準廣東話,落入陷阱之時還會說句:「丟那媽!」不知廣東將領聽見作何感想?文章結尾劉火子還是禁不住抒情,心痛的卻只能是被日人虐待無辜慘死的母豬。
九
歷史的端倪總是通過後見之明被發現的。入口之處可以成為出口;太平洋戰爭既是被炸斷的故事尾巴,卻也潛伏了故事的開端。如此,舒巷城和易文這兩個成名於五十年代香港的文人,便無法不成為上場的主角。收在本卷中,舒巷城的兩篇試筆之作,以及易文從上海投到香港的作品,也就成了指向未來,蛇舌分岔的暗示。
一九四一年,日軍向香港開火前不久,舒巷城的父親過世,遺下妻兒以及筲箕灣一家小小的「汽水店」。當時二十歲的舒巷城已經開始創作,以王烙的筆名在報刊上投稿,和較年長的友人出版過詩集《三人集》,並在此時因為日軍抵境而迫於自行燒毁。本卷收入發表於一九三九年的兩篇〈朱先生〉及〈歌聲〉,正如舒巷城自言,頗受到一些南來文人的影響。這兩篇作品鼓吹抗日,大概在舒巷城燒毁的文稿之列。不久以後,舒巷城不欲久處皇軍統治的淪陷區,隻身到內地工作,飄泊流轉,一九四八年才重返香港。年近三十的流浪者帶着雙重的視域,繼續把這座城市低下層的生活寫進他的小說,然而記憶錯置,對於香港,陌生熟悉之感,或如〈鯉魚門的霧〉裏梁大貴之於鯉魚門:「我是剛來的……」。(64)
沿易文,我們可以追縱到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軌跡。一九四○年,二十一歲,出身世家的易文(當時仍以本名楊彥岐發表作品),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然而在好友穆時英、劉吶鷗相繼被暗殺後,不得不避難乘船到香港。因為早前於香港《大風》的投稿,易文受主篇陸丹林賞識,來港時得到特別的照顧。(65)就像張愛玲,那時以上海人自居的易文,多少認為香港不過上海的劣質翻版。到港半年,他寫的文章裏充滿了對香港文化的揶揄。不過,香港緊貼世界電影的脈搏,易文倒認為是上海所比不上的。(66)一九四○年他來港以前,發表於《大風》的一篇小說〈午夜十二時〉,以蒙太奇的手法,向香港的讀者剪影上海不同階層的都市生活。當時易文大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於一九四九年定居香港,以易文之名,續寫都市小說,並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最重要的導演之一。在他的電影中,總是有那麼一個載歌載舞的女子,青春燦爛,自由獨立,彷彿新生活就在眼前。
* * *
本卷所選小說來源,主要為《香港文學大系》工作組所建資料庫、本地大學所藏部分香港報刊、單行本及數種期刊數據庫。目前所見香港早期報刊版本,缺漏甚多,字跡模糊至不可讀者亦不少;另外,尚有許多本地、外地所藏的舊書刊未及蒐集,皆本卷局限。二、三十年代刊行的作品,不少字體與標點用法與今日不同,印刷上的錯漏也較多。《大系》以盡量保留原文風貌為原則,進行了若干校訂統一,亦請讀者留意。《小說卷一》囿於我個人視野與學識,錯漏處,望專家讀者指正,也盼望日後能有更多被遺忘的作者、作品能被重新發現。
感謝《香港文學大系》編委的信任,邀請我參與這次計劃,並予以編選上極大的自由度;導言初稿,獲多位指正,並給予寶貴意見,亦在此致謝。編委當中,好幾位是本人大學及研究院時期的老師,開闊了我對(香港)文學的眼界,令我受益至今,也希望在此表示謝意。在我加入《大系》編選工作時,工作小組已整理、掃描多份重要報刊及單行本材料,大大減少了編選的困難;李卓賢慷慨借出珍藏書籍;編選時許多繁瑣問題,常得賴宇曼協助解決;選編作品,得何杏園協助初校,葉寶儀多次到香港大學圖書館幫忙打字,皆在此衷心致謝。最後,我得感謝前人留下繁花似錦的小說,它們帶給我許多美好的時光。

• 《小說星期刊》第一期(一九二四年八月)封面

• 《南中報晚刊·說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其中小說類分「軼事小說」、「砭世小說」、「俠情小說」、「社會小說」。冰心〈離家的一年〉由此日起連載,被歸入「社會小說」

• 《伴侶》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封面

• 《伴侶》第五期(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目錄頁

• 《字紙簏》第二卷第一號(一九二九年)封面

• 羅西等著《仙宮》(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七)書影

• 《仙宮》書後廣告

• 龍實秀《深春的落葉》(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八)扉頁

• 侶倫〈愛的巡禮者〉連載之二,刊於《大光報·大光文藝》(一九三○年八月三十日)

• 《工商日報·市聲》(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 刊於《南華日報》(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之「廣九鐵路行車時間表」

• 刊於《南華日報》(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之廣告

• 《立報·言林》(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

• 《南華日報·一週文藝》(一九四○年五月廿五日)。該報支持汪精衛政權,並宣傳「和平文藝」

• 《南華日報·一週文藝》連載漫畫「必勝先生」(一九四○年三月九日)

• 《時代文學》創刊號(一九四一年六月)目錄頁
註釋
(1) 布魯諾·舒茲著,林蔚昀譯〈天才的時代〉,《沙漏下的療養院》(臺灣:聯合文學,二○一四),頁二十七。
(2) 指明「華文」小說,因為不忘尚有其他在香港以不同語言書寫的作品。《香港文學大系》關注的,僅限於華文創作。
(3) Roland Barthes,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trans. "What is Writing?" Writing Degree Zero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9.
(4) 盧瑋鑾從七十年代開始保存、整理及研究香港文學的資料。以這些資料為基礎,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於一九九八年出版《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乃目前二十至四十年代香港文學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
(5) 關於最早有意識的「香港文學」研究,不少學者會提及一九七二年《中國學生周報》所發起的討論,以及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學文社舉辦的「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後編印成《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資料彙編》)。然而,大規模的研究與書寫,則須於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確定香港前途的八十年代才開始。可參考羅貴祥〈「後設」香港文學史〉,羅貴祥編《觀景窗》(香港:青文書屋,一九九八),頁一五九至一六一;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五十七至七十五;陳滅〈文化、政治和「國家需要」——香港文學研討會的非文學牽連〉,《Magpaper》第二十八期(一九九八年五月)。
(6) 同人〈賜見〉,《伴侶》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
(7) 編者〈Adieu——並說幾句關於本刊的話〉,《鐵馬》第一期(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
(8) John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第二十六期《香港:本土與左右》(臺北:聯經,二○一四年十月),頁一一三至一五一。
(10) Norman Miners,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1911 to 1941,"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27.
(11) 侶倫〈島上的一群〉,《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一九八五),頁三十二;葉輝〈三十年代港滬現代詩的疾病隱喻〉,《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青文書屋,二○○一),頁三○八。
(12) 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一九八七)。
(13) 陳順馨〈香港與四○至五○年代中國的文化轉折〉,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恆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二○一一),頁五十七至七十八。原題〈香港與四○-五○年代的文化轉折〉,刊於陳平原編《現代中國》第六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五年十月),頁一七六至一九六。
(14) 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二○○三),頁二○七至二四一。
(15) Jacques Derrida,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5.
(16) 黃子平〈香港文學史:從何說起〉,《害怕寫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五),頁五十八。
(17) 魯迅〈略談香港〉,原刊於《語絲》週刊第一四四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五),頁四四六至四五六。
(18) 如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即持這種看法。參考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一九九九),頁七十一至七十三。
(19) 黃康顯〈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頁十八至四十二。
(20) 根據香港的人口普查,一八九一年,香港人口約二十二萬,外籍人口約一萬;一九三一年香港人口約八十五萬,外籍人口約二萬八千,來自四十八個國家。資料轉引自丁新豹、盧淑櫻〈序:多元民族建構的香港社會〉,《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商務印書館,二○一五)。
(21) 袁昶超認為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內容兼及中英,但以中文為主,可算是中國最早的民辦報刊之一;也是香港最早的中文新聞刊物。所謂民辦,指的是由民間編纂,同時內容不同於清朝半官方的「京報」(消息多來自官方)。袁昶超認為中國的民辦報紙,主要源起於外國教士傳播教義,以及革命志士宣傳革命之目,《遐邇貫珍》的主編即為英國傳教士麥度斯(Walter Henry Medhurst)。一八七三年,王韜與友人購下《遐邇貫珍》的印刷設備,於一八七四年創辦《循環日報》,是華人辦報獲得成功的最早一家。至於中國人主編的《中外新報》(英文《孖剌報》的附刊,據卓南生考據,約創刊於一八七三年),袁昶超形容為「中國現代新聞報紙的第一種」。參考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香港:新聞天地社,一九五七),二十一至二十七;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二○○○),頁五十六至六十四。
(22) 許翼心〈辛亥革命與香港的文界革命〉,《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大學出版社,二○○○),頁八十。
(23) 如冰心〈離家的一年〉,《南中報·晚刊》(連載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廿四日期間)。
(24) 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一三二至一三三。侶倫〈寂寞地來去的人〉,《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一九八五),頁三十。
(25) 黃天石《新說部叢刊·第二集·白話短篇小說》(上海清華書局,一九二一)。
(26)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0.
(27) 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頁一三二至一三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一年》(香港:天地,一九九八),頁二十二至二十四。
(28) 據平可回憶,一九三九年,當龍實秀邀請他替《工商日報》「市聲」撰寫連載小說時,對自己的創作態度,有這樣的反省:「我從事創作時老是有意無意地以『自己』為中心,所寫的是自己喜歡的東西,而自評優劣時也以自己的喜惡為標準。但我逐漸察覺:這個態度只適宜於撰寫留供自己欣賞的文章;如果文章是準備發表的,那就不能不理會讀者。至於迎合讀者到甚麼程度,那是另一個問題。」為要寫出為一般市民所喜讀的連載小說,平可還表示「我天天讀傑克的小說,自問獲益不淺。」參考平可〈誤闖文壇憶述(六)〉《香港文學》第六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頁九十八至九十九;〈誤闖文壇憶述(續完)〉《香港文學》第七期(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頁九十四至九十九。
(29) 關於黃天石生平的詳盡評述,參考楊國雄〈傑克:擅寫言情小說的報人〉,《文學評論》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二月),頁五十四至六十二。
(30) 據侶倫回憶,在一九二七年前後,香港報紙已紛紛開闢以白話創作為主的新文藝副刊,參考侶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向水屋筆語》,頁九至十。
(31) 作品原題「劇場裏」,發表於《幻洲》第一卷十二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作品收入小說集《貞彌》時,改題為「La Bohème」。
(32) 一九二六年由美國導演金·維多(King Vidor)所拍攝的默片La Bohème,據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歌劇La bohème改編。
(33) 彭小妍認為,不同於隨波逐流的摩登男女,浪蕩子通過對「當下的諧擬英雄化」,來達到創造和轉化,因而表現出雌雄同體的特徵。至於他們追求的摩登女郎,不過是他們不完全的她我。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跨文化現代性的真髓〉,《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二○一二),頁二十至五十二。
(34) 謝晨光〈加藤洋食店〉,《幻州》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35) 謝晨光〈加藤洋食店〉,《貞彌》(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九),頁三十三至四十六。
(36) 吳錫河〈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第九十八期(一九九三年,二月),頁六十四至六十六。
(37) 羅西〈序〉,廣州文學會編《嬰屍》(香港:受匡出版部,一九二八年四月),頁一至二。
(38) 這點除了可以從雜誌文章風格看出來,他們惹火的舉措,還包括揭發《伴侶》一篇抄襲的文章。《伴侶》第一期刊出了雁遊〈天心〉一文,被發現襲自《小說月報》十一卷十一號的〈一元紙幣〉(署名Anries Williams著,毅天譯)。《字紙簏》嘲諷指證之餘,在第一卷第五號,把〈天心〉一文置於雜誌之首,全文刊出,並附以《小說月報》的原譯以供對照。
(39) 訪問所記為「袁昶球」,疑為「袁昶超」之誤。見吳錫河〈同根相連的鮮花——訪歐陽山談香港文學〉,頁六十四至六十六。
(40) 據李育中的回憶,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香港文學開始出現了較強的政治意識與社會關懷。參考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黃康顯亦認為,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件是香港文學界民族意識的觸發點,參考黃康顯〈抗戰前夕的香港文藝期刊〉,《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五十至六十。
(41) 據侶倫的回憶,魯衡年輕時因在美國從事苦工,患上嚴重風濕,終至雙腳癱瘓,回港後從寄情文藝創作。參考〈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頁二十。
(42)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印度泛指今所說的南亞。有關香港早期南亞裔人的歷史,參考〈南亞裔:警察與商人〉,《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一四五至一六三。
(43) 張初〈張稚廬的〈夫妻〉〉,二○○三年三月《香港文學》總二一九期,頁七十七至七十八。
(44) 平可〈誤闖文壇憶述(六)〉,頁九十八至九十九。
(45) 許定銘〈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大公報》(二○○七年二月二十五)。
(46) 杜格靈〈時代的反叛者〉,《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一九三○),頁八。
(47) 杜格靈〈文藝的霸術〉,《秋之草紙》,頁三十七至四十。
(48) 張愛玲〈燼餘錄〉,《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頁四十八至五十九。
(49) 參考李育中〈小說家羽衣女士是誰?〉,《新晚報》(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據張稚廬所說,《伴侶》雜誌上以「女士」之名發表的作品,卻非偽冒,甚至有不少譯者,故意隱去其女性身份。稚子〈碎話三則〉,《伴侶》第八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頁三十一。
(50) 參考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頁一二六。
(51) 據許定銘所記,侶倫《紅茶》(一九三五年版)一書內頁有「島上社叢書」六本,其中一本為哀淪女士的短篇小說集《婉梨死後》,當時尚未出版。參考許定銘〈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
(52) 葉漢明〈香港婦女與文化傳統及其變遷〉,《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一九九九),頁一一七至一五九。
(53) 錢理群〈漫話四十年代小說思潮〉,《對話與漫游:四十年代小說研讀》(上海:上海文藝,一九九九),頁十至二十五。
(54) 根據一九一一年的香港人口調查,當時男女比例接近三比一。可以想像,辛亥革命前後,社會裏匯聚了大批沒有或未帶家眷的單身男子。到了一九三一年,男女比例大幅拉近,黃康顯認為,香港當時已形成了一個定居的社群。參考黃康顯〈香港情懷與文學情結﹣﹣論詩人劉火子〉,劉麗北編《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一○),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55) 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頁一三○。
(56) 侶倫〈超吻甘〉(CHEWING GUM),北京《圖畫周刊》第十二卷第十七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始連載(雜誌資料不全);後收入侶倫《伉儷》(香港:萬國書社,一九五一),頁一至三十。
(57) 作品改寫後,曾題名〈輝輝的夢〉,刊於侶倫等著《輝輝的新年》(香港:學生文叢社,一九四九),頁十一至十五;後改題為〈輝輝〉,見侶倫《伉儷》(香港:萬國書社,一九五一),頁八十六至九十三。
(58) 例如曾連載於《伴侶》第六至九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的〈殿薇〉,經修改後,改題為「朱莉莎的煩惱」,以立凡之筆名,發表於《華僑日報》(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二十八日)。一九三○年八月期間發表於《大光報·大光文藝》(目前所見報章不全)的〈愛的巡禮〉,經修改後,以胡旋之筆名,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九日期間,連載於《華僑日報》。
(59) 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可參考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9-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二○一一)。
(60) 參考陳順馨〈香港與四○至五○年代中國的文化轉折〉;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9-1949》。
(61) 許子東〈序言〉,侯桂新《文壇生態的演變與現代文學的轉折:論中國現代作家的香港書寫,1939-1949》,頁一至二。
(62) 陳順馨〈香港與四○至五○年代中國的文化轉折〉,頁七十三。
(63) 劉火子二、三十年代在香港發表的小說,最少還包括一九三三年九月於《天南日報》連載的小說〈絕望〉,詳見〈劉火子生平及文學創作簡歷〉,《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頁二七三至二八五。
(64) 本篇寫於一九五○年,參考舒巷城著,秋明編《舒巷城卷》(香港:三聯,一九八九),頁一○六至一一二。
(65) 易文著,藍天雲編《有生之年:易文年記》(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二○○九),頁五十四。
(66) 楊彥岐〈香港半年〉,《宇宙風·乙刊》第四十四期(一九四一年),頁三十至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