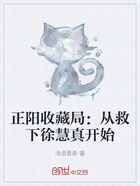
第10章 绢帛上的交锋
修缮室的煤炉“咕嘟咕嘟”吐着白气,混着胶矾水的酸涩在青砖地上漫开。苏浩然的的确良衬衫第三颗纽扣用别针别着——那是上周给学生补课时被扯掉的,徐慧真用陈雪茹送的杭绣线临时固定,针脚细密得像画中王希孟的隐笔。他的解放鞋边沾着正阳门的黄土,在铺着青砖的修缮室里踏出浅灰的脚印。
“苏老师,”李大娘的五角星徽章歪向一侧,露出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内衬,“张师傅最见不得年轻人空谈。”她的小本本封面是 1954年的《粮食供应证》,内页夹着半张过期的布票,“去年他把故宫画学班的学徒骂哭三回,说‘修画要像蒸窝头,得扎实实地下苦力’。”
话音未落,穿对襟夹袄的汉子“咣当”一声砸了修复笔,山东口音震得煤炉上的铜壶跳起三寸高:“黄口小儿懂个棒槌!”他袖口的石绿粉末簌簌掉落,在画案上积成小小的青峰——正是故宫修复组的“快手张”,袖口还露着纹着“精忠报国”的小臂,那是年轻时被师傅用烟袋锅烫的刺青。
苏浩然的目光落在画轴上,系统界面正以红色标注十七处金粉隐笔的氧化点:「检测到宋代‘洒金叠染法’,鹿胶配比误差需控制在三钱二分」。他摸了摸虎口处的粉笔茧,那是每天在黑板上写满三黑板字的印记,开口时带着课堂上的清晰条理:“修缮此画需过三关——材料关在矿物颜料,笔意关在少年锐意,融合关在新旧火气。”
“放你娘的臊!”快手张踢了踢脚边的解放鞋,鞋底补着三层胶皮,“老子修《韩熙载夜宴图》时,你小子还在玩泥巴!”他指向画中剥落的峰峦,“就说这石绿,现在上哪儿找解州老匠人磨的‘孔雀石’?去年‘破四旧’把琉璃厂的石碾子都砸了,全换成‘爱国绢’‘跃进胶’,修出来的画跟贴报纸有啥区别?”
石先生的白胡子抖了抖,圆框眼镜后的目光却落在苏浩然的帆布包上——露出半截刻着“耕读传家”的善琏湖笔,笔杆包浆温润,分明是光绪年间的老物件。作为故宫修复室的老匠人,他认出这是当年溥仪带出宫的旧物:“苏老师说的‘少年锐意’,可是指王希孟作画时的‘以燥破润’技法?”他用竹尺轻点隐笔处,“此处金粉氧化,倒像是正阳门老窑砖的火漆印。”
苏浩然心中一动,系统界面闪过正阳门老窑的朱砂标记:“正是。王希孟的笔锋里藏着股子狠劲,像极了咱正阳门的煤炉——新煤块得接住旧火,才能烧成通红的炭。”他忽然从帆布包取出牛爷给的拓片,“诸位看这‘石如君子’的题跋,笔锋转折处的力透纸背,和老窑砖的煅烧火候如出一辙。”
戴老花镜的陈教授咳嗽一声,摸出个铁皮盒,里面躺着指甲盖大的石绿碎块:“这是宣统年间的存货,当年从养心殿搬出来的。”他镜片后的目光带着试探,“苏老师说的七蒸七晒,可是《天工开物》里‘石绿三制法’?”
“需要搭配鹿胶,”苏浩然注意到系统界面亮起“古法矿物提纯术”的解锁进度,“而且补笔时得用‘童子功’——不是技法,是心境。王希孟十八岁作画,既有宫廷的工整,又有民间的野趣,就像咱正阳门的孩子,拿粉笔能算算术,握毛笔能画竹石。”
快手张忽然站起身,夹袄带起的风掀动桌上的修复方案:“说了这么多,敢不敢临半幅‘层峦叠嶂图’?”他指向墙角的宣纸,“用我的松烟墨,按宋代笔意。”
李大娘的手在苏浩然后背轻轻推了推,掌心的老茧带着鼓励。苏浩然走向画案,砚台里的墨汁还带着快手张的笔锋——焦糊味里混着一丝松脂香。他蘸笔时,系统模拟的王希孟笔意在视网膜上展开,十八岁少年的锐意与他给学生画算术图解时的耐心奇妙融合,笔尖在宣纸上疾走,先以淡墨勾出山骨,再蘸石绿扫出峰巅,在转折处故意留下飞白——那是少年人控制不住的锋芒。
修缮室的煤炉突然安静,只有笔尖划过宣纸的“沙沙”声。快手张的修复笔“当啷”落地,他难以置信地凑近:“这……这是失传的‘劈笔皴’!故宫档案里记着,只有王希孟用过!”他的山东腔突然软了,袖口的石绿粉末落在苏浩然的临本上,像撒了把星星,“后生,你这笔锋里的狠劲,倒像是从正阳门的老窑里烧出来的。”
石先生的白胡子笑出了金粉,他握住苏浩然的手,掌心的老茧与年轻人的粉笔茧相触:“老夫错了。你不是黄口小儿,是带着人间烟火气的修画人。”他指向画中隐笔,“当年徽宗题‘青出于蓝’,如今应在你身上——用粉笔教算术的手,一样能握稳羊毫笔。”
李大娘的小本本“沙沙”记着,把“老窑砖”“解州石绿”圈了又圈:“我这就给解州文化馆写信,就说BJ的修画匠人要‘抢救老手艺’!”她摸出半张粮票,“中午带苏老师去职工食堂,凭这票能换半碗红烧肉——比小酒馆的酱牛肉肥。”
修缮室外,雪停了,阳光穿过冰花窗,在苏浩然的的确良衬衫上投下千里江山的影子。快手张蹲下身,用修复笔在地上画了个“窑”字,抬头时山东腔里带着难得的柔和:“后生,你在正阳门教的那帮娃娃,下周带过来吧。让他们看看,老匠人怎么把碎了八百年的江山,一片片粘回绢帛上。”
当石先生铺开新的修复方案时,修缮室的门“咣当”推开,通讯员举着加急电报一路小跑:「解州蒲州石绿匠人已登火车,随带祖传磨石与《颜料密录》」。快手张的修复笔在“笔意关”三字上画了个圈,忽然哼起山东快书:“王希孟,十八岁,千里江山笔下现;小苏老师二十三,粉笔羊毫两头尖……”
雪光映在画轴上,苏浩然看着画中绵延的群山,忽然觉得每处破损都是时光的馈赠。他的帆布包带勾住博古架上的老棕刷——木柄裂了缝,用铁丝缠着继续用,恰如这个修补的年代,连古老的绢帛都在等待,等待一群带着粉笔茧与老匠气的人,让八百年前的月光,重新照亮 1955年的煤炉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