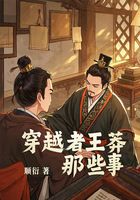
第2章 王氏的显赫家族
王氏家族的显贵,得从王莽的姑母,王政君谈起。话说在李亲本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1年,王政君出生的那天,似乎天意也特别眷顾她。
那晚,李亲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轮明月飘入她的怀中,似乎暗示着这个孩子命中注定不凡。王政君长大后,温文尔雅,端庄贤淑,颇具妇人之道,大家都说她是“得天独厚”。但她的婚姻却颇为波折。曾经,她被许配给一位男子,可惜未及成婚,那男子便突然死去。后来,她又被东平王选中,作为姬妾,然而婚事未成,对方又死了。
王禁为此心生疑虑,便请了占卜之人来相面。这位卜者见王政君一眼,几乎没有停顿地说:“当大贵,不可言。”这话一出,王禁心中更为惊异,便命令王政君研读经典,学习琴棋书画,浑然不知,这位女子日后的命运,早已注定。
时间流转,到了公元前55年,王政君已经十八岁,按常理说,这个年纪在汉朝的女子已不再算年轻了。然而她依然未曾婚配,这一次,她被选入披庭,成为“家人子”,也就是宫中的一员。
大概在同年年底,皇太子的爱妾司马良娣,因病重而死,临终时她对太子说:“我命不该如此,我是被你的那些妃嫔们给诅咒死的!”她的死让太子悲伤过度,身心俱疲,也因此对那些妃嫔们心生怨恨,再也不与她们亲近。
宣帝察觉到太子心情郁结,知道他对宫中的妃嫔们已经心生厌恶,便让皇后从家人子中挑选几位娴静淑女侍奉太子。于是,王政君与四名其他女子被选中,站在一旁等待太子的审视。
当天,太子前来朝见,众女子列席,他并没有对谁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便随口答道:“其中一人可以。”长御见太子离王政君最近,而且她那身绛色大掖衣格外引人注目,便以为太子青睐她,于是立刻安排王政君进入太子宫中。
没过多久,王政君便怀上了太子的孩子。虽然太子宫中早已有十多位妃嫔,但没有一位能够生育,偏偏王政君进宫不久便怀孕。甘露三年,她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宣帝得知这个喜讯后,欣喜若狂,亲自为孙子起名,取名骜。每次见到孙子,都会抱在怀里,亲自逗弄,爱护有加。
转眼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去世,太子即位,称为孝元帝。王政君在短短的三天内,从婕妤被立为皇后,王禁也被封为阳平侯。王禁一跃成为了皇室的亲贵,王家的地位也因此扶摇直上。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任命为长乐卫尉,成为了皇后的侍卫。
不过在这些荣光背后,仍旧潜藏着暗流涌动。永光二年,王禁去世后,王风继承了侯爵,但宫中的风云早已变幻莫测。汉元帝是一位喜新厌旧的帝王,渐渐疏远了王皇后。与此同时,宫中傅昭仪的宠爱渐增,她为元帝生下了儿子——即后来的定陶共王。定陶王聪明好学,才艺出众,深得元帝宠爱,甚至可以随同元帝一起坐上侧席,随行也总是紧随其后。
随着元帝健康的日渐衰退,他渐渐将政事交给了大臣处理,自己沉浸于音乐的世界,成天敲鼓、击铜丸,享受自娱自乐的乐趣。他喜欢将鼓放在殿下,然后凭栏而立,自己投掷铜丸,若是能打准鼓的节奏,便极为高兴。宫中的妃嫔和宦官们纷纷效仿,却始终达不到元帝的水平,只有定陶王能够与之匹敌。这让元帝的自豪感更加膨胀,他屡屡称赞定陶王的才能,使他深得宠幸。
时任马都尉侍中的史丹是太子党,他看到汉元帝宠信过度,便跑来觐见道:“所谓有才能,指的是聪敏好学,知识丰富,太子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把音乐当成才能,那宫里的乐师都能担任宰相了。”
汉元帝听完,不好反驳,只是嘿嘿地笑,依旧如故。
建昭四年,元帝最小的弟弟中山哀王去世,太子与这位小叔一同长大。元帝对中山王的死十分痛心,他带着悲伤去吊唁,而太子却在灵前面无表情,毫无哀伤之意。元帝愤怒异常,怒斥太子:“怎么能有如此冷酷无情之人,怎么能担当起父亲的责任?”
史丹看到这一幕,迅速判断形势,立刻跳出来为太子辩解。他恭敬地摘下帽子,走到元帝面前,向他谢罪:“臣见陛下悲伤过度,深怕损害御体,特告戒太子避免表现过度伤心,实在是我的过失,请陛下责罚。”
史丹这一番话,成功化解了元帝的怒气,也无形中保护了太子。如此,宫中的风波暂时平息,但王政君与元帝之间的矛盾,却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病重,几乎无法起身。病榻前,傅昭仪和定陶王守在一旁,心神不宁,而皇后与太子却难得一见。元帝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废太子另立定陶王的念头也愈加强烈。定陶王和他的亲信早已在暗中筹划,向尚书询问当年汉景帝如何废除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事。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宫中上层的众人也心生疑虑,皇后和她的哥哥王凤愁云满面,百思不得其解。
那日,元帝稍显独处,史丹抓住了时机。当时元帝虚弱地躺在床上,目光黯淡无光,史丹沉默地跪倒在床前,双膝着地,低头叩首,眼中泪光闪烁。他说话时语气急切而悲戚:“陛下,太子已经做了十多年太子,百姓的心已向他归属,现在外面流言四起,言说太子的地位动摇。若真如此,恐怕天下群臣会誓死守护,谁也不敢听从命令。倘若陛下有意废太子,还请先赐我死以昭示众人!”
元帝听罢,心中一震。他性格仁弱,缺乏坚定主见,面对史丹的一片忠心,最终动摇了。
史丹的言辞诚恳,悲恸的声音令他心生感动。他低叹一声,目光迷茫,“朕身体日渐不如人,太子与两个王子都尚幼,我一直疼爱他们,时时挂念他们。决不想废立太子的事情。皇后一向谨慎,先帝也一直喜爱太子,我怎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驸马都尉的言论究竟从何而起?”
史丹心中一块大石终于放下,他急忙再次叩头,“愚臣冒昧言之,罪该万死!”
元帝见史丹如此忠心,感动于其言辞得体,决定放下废立太子的念头,转而采纳了史丹的意见。“史丹,朕病日渐沉重,恐怕无望好转。死后,你一定要辅佐太子,不可辜负我的一片心意。”史丹愣在原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心头的责任感愈加沉重。
元帝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汉成帝。新帝登基之时,心中最感激的人,便是史丹。他不仅为自己保住了太子的地位,还帮助他稳定了局势。因此,成帝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提升史丹为长乐卫尉。不久后,史丹被升为右将军,并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很快,他的职务和荣宠都水涨船高,被任命为左将军、光禄大夫。成帝深知史丹功劳,鸿嘉元年时,再度封他为武阳侯,食邑更是达到一千一百户。
史丹的生活开始富贵荣华,享尽了当时所有的奢华和美味,他的九个儿子也因父亲的庇护而皆为侍中,左右亲近,富贵满门。
与此同时,王政君在宫中的地位也是日益巩固。此时她已三十八岁,经过二十年的宫闱生涯,她早已习惯了这座皇宫中的尔虞我诈,尤其是那种关于权力的博弈。她深知,只有将自己的亲人们一一提拔,才能确保自己在宫中的权势不被削弱。
而成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帝王,却正处在青春期的狂热之中,纵酒纵色,对国事漠不关心。朝政基本上由她的舅父王凤代为处理。成帝更愿意沉迷在寻花问柳的欢乐中,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却全然不理。
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王政君的同母弟王崇病故,这对她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她的心中,愈发燃起了提拔家族成员的决心。于是,第二年,她借着成帝的名义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五个兄弟同日封侯,人称“五侯”。
王政君更是巧妙地安排了母亲李氏的归来,让她在家族的背后有了更强的支撑。她让李氏给苟氏所生的苟参也获得了一些封赏,尽管成帝曾有所反对,但最终苟参还是得到了侍中水衡都尉的位置,王政君的布阵显得更加牢固。
随着王家兄弟们地位的不断提升,他们开始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史书中说他们“赂遗珍宝,后宫姬妾数十,僮奴成群。”
宫中的生活变得富丽堂皇,王家大院也日益豪华,犹如一座座辉煌的城堡。百姓的歌谣流传开来,讥讽着他们的奢靡:“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七山渐台西白虎。”尽管这些歌谣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生动地反映了民众的对王家的怨恨。
儒生如王章等人,纷纷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批评王氏家族。刘向也敢于公开上书成帝,直言王家依赖权势骄奢腐化,“五侯僭盛,作威作福”。王政君深知外界的批评,曾在成帝面前泪流满面,时常为王家的未来担忧。她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家族的稳定和荣华,但是外界的声音却愈加尖锐。
就在这一切喧嚣与奢华之下,王政君的政治安排逐渐成型。她的家族在权力的漩涡中越陷越深,而她所渴望的,无非是一个更为稳固的王朝——一个永恒的权力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