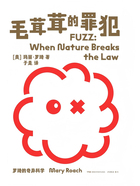
导语
1659年6月26日,意大利北部某省五个小镇的代表联合起来,正式起诉毛毛虫。原告方痛斥这种当地物种侵入居民们的花园和果园,连吃带偷。法庭发出了传票,复制了5份,钉在每个小镇周边森林里的树干上。传票上写得很清楚,被告毛毛虫必须于6月28日的规定时段出庭,法庭会给它们指派法律代理人。
当然,到了法庭指定的时间,毛毛虫没有露面,但照例进行了缺席庭审。尚存的一份文件中写道:法庭认可毛毛虫有权利享有自由、快乐的生活,但前提是不会“损害人类的幸福”。法官判决如下:毛毛虫将被分到另一块区域,以便存活和享乐。法庭制定出这些细则时,被告早已完成了大破坏,溜之大吉,化蛹成蝶。官司就这样打完了,毫无疑问,原告和被告都很满意。
1906年出版的《针对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详细介绍了这个案件。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还有点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存心搞噱头的书?书里写到了被逐出教会的几只熊。还有收到3次警告、不得阻挠农民设网捕猎的蛞蝓,否则将被予以刑罚——“砸扁”。但是作者很快就让我折服了,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大海捞针,从古老文献中收集到了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附录中收入了19份以原始文字记录的相关文件副本。我们可以看到法国警察在1403年审判了一头犯下凶杀案的母猪,并提交了1份费用清单(“为了把它关进监狱,花了6索尔[1]”)。我们还能看到发给老鼠、并推入老鼠洞的驱逐令。在1545年众葡萄酒商对一种绿色象鼻虫的投诉中,我们不仅能知道律师们的大名,还能见识到他们如何善用“诉讼拖延”——堪称这种历史悠久的法律策略的古早范例。据我所知,这场官司拖了八九个月——不管是几个月,反正比短命的象鼻虫拖得久。
我搬出这些例子并非要证明过去的法律制度有多愚蠢可笑,而是为了说明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的冲突由来已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难以解决的,直到现在,处理这类问题的专业人员也深知这一点。当大自然里的动植物违反了为人类制定的法律时,究竟怎么办?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地方法官和高级教长显然不是在理性层面做出这些决策的,毕竟,老鼠和象鼻虫读不懂“物权法”,谁也不能指望它们能谨遵人类文明的道德准则。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要以威慑力镇住老百姓:都来瞧瞧吧,即使是大自然也得臣服于我们的统治!从这个层面看,确实不走寻常路,绝对令人难忘。16世纪的法官善心大发,对子嗣满堂的鼹鼠予以宽大处理,不仅能彰显权威,还表明了他执法有度,体恤民情。
徜徉在中世纪及其后几百年的历史中,我不禁思忖:现代文明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产生新的影响和改变?看够了中古法庭和教会所做的稀罕决策,我转而去探究科学界对此有何建树,又为未来提供了哪些新思路?就这样,我越走越远。我的“向导”们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头衔:人象冲突专家、熊类主管、危树爆破工。我和掠食动物攻击专家、攻击现场取证调查员、激光驱鸦设备制造者、温和毒杀饵药测试者共处了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些“热门地点”——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的后街暗巷,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饱受豹子威胁的小村庄、梵蒂冈城进行教宗主持的复活节弥撒前夜的圣彼得广场。我回顾了经济鸟类学家、鼠类搜捕者等专业人员曾经做出的贡献,也思索了未来的管理者、保护遗传学家们能够达成的伟业。我亲口浅尝了老鼠饵料的滋味,还被一只猕猴打劫了。
请恕本书无法面面俱到。在200个国家里,有2 000个物种经常会做出一些与人类产生冲突的行为。每个冲突局面都需要针对环境、物种和利益相关者的特定解决方案。你在本书中看到的是两年探索期中的高光时刻,那是一段让我踏入先前闻所未闻世界的奇妙旅程。
本书的前半部分涉及重罪:谋杀和过失杀人、连环杀人、严重伤害、抢劫和非法入侵、盗尸、葵花籽大盗。罪犯包括熊虎豹这类常见的嫌疑犯,以及一些不太常见的——猴子、乌鸫、花旗松。后半部分的几个章节涉及不太严重,但更普遍的轻罪。我们将谈及乱穿马路的有蹄类动物,无缘无故大肆破坏人类财产的秃鹫和海鸥,制造污物的鹅,非法入侵的啮齿类动物。
当然,抠字眼的话,这些都算不上“犯罪行为”。因为动物遵守的不是法律,而是本能。几乎无一例外,本书中的野生动物们只是在做动物该做的事:进食、排泄、安家、保护自己或亲生的孩子。它们只是碰巧对人类,或人类的家园,或农作物做出了某些举动。但不管怎么说,矛盾和冲突是存在的——让人类和市政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困境,让野生动物的生存变得更艰难,还为某人提供了素材,写一本偏门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