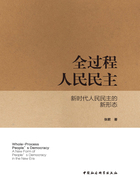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民主建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中国人民开启了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人民民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一 协商建国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解放战争并未完全结束,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开展土地改革,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的条件尚不具备,人民代表大会短时间内没法立即召开,协商建国和实行过渡性的民主政治体制成为当时的必要选择。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9]。这一号召发布后,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纷纷响应。从同年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应邀从全国各地及海外赶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专门向政协代表做出明确说明:“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现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0]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同时,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对其他政治制度也做出了重要安排。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一纲领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31]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并由它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共同纲领》还明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在之后也会继续保留。在民族政策部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二 新中国第一次普选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一运动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由此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斯大林两次与他谈话,明确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制定宪法。中共中央认真考虑并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提前召开全国人大并制定宪法。[32]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必须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及时地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用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替现在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决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3]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即行筹备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同年3月1日公布施行。正如邓小平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的,“选举法的颁布正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34]。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省、县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每个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35]作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类型的选举法,《选举法》为新中国开展第一次普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4月3日,根据《选举法》成立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两份文件,新中国第一次普选人民代表正式拉开。
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中国各地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当时,除少数暂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地区外,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有214798个,开展基层选举地区的人口达到5.7亿多人,登记选民总数占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参加投票的选民共2.78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5669144名基层人大代表。1954年6月至7月,全国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以及县一级单位和中央直辖市的170个区分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668万人。同年7月底至8月中旬,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共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136人。此外,军人代表大会、侨务扩大会议分别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0人和30人。这样一来,除台湾因尚待解放而名额暂缺外,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36]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普选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民主实践。它在显著推动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热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观念,也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此后一直到196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3届,共10次会议,对于保障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五四宪法”的制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在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下起草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五四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提交大会正式审议前,该宪法草案已经由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社会各方面代表8000多人进行了广泛讨论,收到了5900多条意见。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公布宪法草案,交由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对宪法草案做了阐释,认为这一宪法草案贯穿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个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37]这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全国范围内人民群众的讨论热情空前高涨。近3个月时间里,共有1.5亿多人参与讨论,累计提出118万多条修改和补充意见,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了根本性法律保障,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宪法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即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普选产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原有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同时在正文中从根本法的高度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宪法还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年满18岁后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并且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职能的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65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届,12次会议。这一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后期虽然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在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行政治协商和提出批评建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发生明显变化。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指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而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任务包括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马列主义。[38]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总纲的规定,依照毛泽东的意见,系统阐述了今后人民政协的五点任务:“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39]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获得审议通过,成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的行为准则以及各级政协设立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依据。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对党和非党的关系首次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年9月27日,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40]为此,在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41]
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开启了人民民主的新纪元,从自身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框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切实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利。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公布施行为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提供了根本性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在协商建国实践基础上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践。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严重挫折,民主和法制遭到极大破坏。从1965年1月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到1975年初都没有召开大会,全国政协直到1978年2月都没有召开会议。这种极不健康的停滞状态产生于更大的混乱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被夺去权力机关的职能,全国政协机关被迫停止办公,各民主党派被勒令停止活动,公民权利遭到大范围的严重侵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