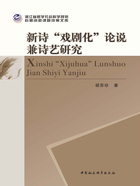
第一章 跨语际实践: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戏剧化”论说
“戏剧化”对中国诗无疑是一种异质的东西,首先得深入中西文学传统辨源。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直觉化、意象化、天人和谐等特质,彰显了东方文化的诗意;在另一类民族,逻辑化、分析式、对立性的思维特征,孕生出宏阔、激荡的史诗(叙事文学)、戏剧艺术。而各自的古代文学传统,又促生着不同的文类秩序。在中国,是(抒情)诗为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西方则以史诗与悲剧担纲,抒情诗居于边缘。当然,随着文明的演进,中西文类秩序也发生了改变,中国的传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后来者居上,抒情诗腾挪出了中心地位,而西方则在近代狂飚运动中涌现了抒情诗的热潮。到了现代,日益深化的文化交流大大丰富了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中西文类秩序也走向趋同,诗歌层面呈合流对话之势。
在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袁可嘉、卞之琳、穆旦、张枣、西川这些优秀诗人诗家的确表达了“戏剧化”“戏剧性”主张或实践。这一现象的发生,只能在现代时间,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互中,也即“跨语际实践”当中。刘禾提出“跨语际实践”观点,意在考察20世纪中西交互过程中新的名词、意义、话语,以及新的表述模式在中国本土语言(即“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她认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1],在她看来,中国文体从古代的文史哲不分家到现代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四分法的“纯文学”过程,实际上是汉语向西方语言翻译、选择新名词并最终获得合法性运用的过程。“跨语际实践”的研究可以深入主客两方语言的等值问题,刘禾不仅从这一层面观照了“国民性”“个人主义”等西方语言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翻译、理解、接受问题,还探究出老舍小说的“自由间接引语”这一“语际表述模式”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意义。用“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和视角来观照,新诗中的“戏剧化”话语包含了西方戏剧诗学传统的影响,尤其是现代时期的诗人,他们的“戏剧化”主张或个体创作与西方近现代诗学、诗歌文本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