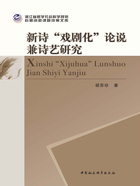
三 问题逻辑
要尝试整体性地进入各种新诗“戏剧化”论说,需跳开袁可嘉“新诗戏剧化”的框架,这样才能考察新诗各个阶段关于“戏剧化”“戏剧性”的话语指涉,辨析历时性差异和关联,区分不同阶段的戏剧化诗学语境及创作机制。关涉新月、九叶诗人戏剧化的指称和史料毋庸置疑,需要注明的是“1990年代”。本书将当代时期“戏剧化”探索限定在“1990年代”或“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因为“1990年代诗歌”多年作为新诗研究专题,产生了许多博士学位论文,早成专有名词,虽然其中的“戏剧化”“戏剧性”未被集中论述,但梳理后可发现,当代的“戏剧化”诗观及写作自觉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诗人当中;另一方面,这些诗人如西川、欧阳江河、萧开愚,在新世纪还继续推出“戏剧性”“戏剧化”文本。纵观各种资料,新诗“戏剧化”理论除了见于袁可嘉的几篇文章,大多时候只是隐现于新诗不同时期的诗人、诗家的概括性主张或写作经验论当中,诗人的理论之间也未言明直接的承继关系,这种发展性、差异性特征,决定了“戏剧化”概念不具有给定的专门内涵。
从中国文学内部看,新诗阶段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戏剧化”一说,站在抒情传统背景上论,这一现象如何观照?从中西横向影响上看,经过臧棣、蓝棣之等学者的梳理,袁可嘉与新批评“戏剧主义”的关系、新月诗人和维多利亚诗人的关系逐渐呈现出来,但中西之间的影响途径、诗学侧重点、借鉴的实际价值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还可进一步具体辨析。尤其是袁可嘉较为驳杂的“戏剧化”理论,涉及瑞恰兹、艾略特、勃克、布鲁克斯、燕卜荪等“英美新批评”理论不同阶段的学者,袁可嘉从他们那儿吸收的“戏剧化”观到底有何区别?在纵向关系方面,各个阶段戏剧化实践的区别与联系值得加以厘清。《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收录的关于“1990年代诗歌关键词”的讨论中便提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谈到的诗学很接近袁可嘉的戏剧主义观念,但不清楚两代之间“哪些东西是相同的,哪些东西是不同的”[33]。诸个层面值得试探究竟。
由于关涉诗歌和戏剧性的交集,围绕个别诗人“戏剧化”写作个性或诗观的讨论也容易产生分歧或追问。如江弱水作为卞之琳研究的集大成者,认为新月师辈文本中的矛盾性、戏剧性在卞之琳那里更加“全面深入”[34];但陈旭光感觉,卞之琳的“戏剧化”是“颇为可疑”的,因为“矛盾冲突性似乎不够”[35]。冷霜则提出,“在‘意境’和主要从艾略特那里得来的‘戏剧化’技巧(它与袁可嘉40年代主要从肯尼斯·勃克那里借来的‘戏剧主义’诗学是需要区分开的两个概念)这两个相当不同的范畴之间,卞之琳将之牵连起来的交叉点在哪里?”[36]这些存疑或可展开讨论。
更普遍的问题在于一些概念混淆。有学者将袁可嘉的“戏剧化”论说等同于倡导“叙事诗”,称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戏剧化论说“为当时的中国现代叙事诗理论建设及批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想活力及启迪”,开启了80年代呼唤史诗的先河。[37]实际上,叙事诗重在故事、人物和主题,和袁可嘉所述关联微末。有研究者还完全照搬袁可嘉“客观对应物”层面的“戏剧化”理论,去对号入座地阐释所有现代派意象诗都是“戏剧化”[38]。可见,一旦机械刻板地照搬袁可嘉驳杂的“戏剧化”说,必然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在笔者看来,结合所有新诗史上的“戏剧化”论说,它们具有内在的共同指向,即都是突破习常抒情诗的特点或规约,化用戏剧美学理念或戏剧精神、戏剧形态元素,丰富和扩展非叙事类新诗的可能。综合几个阶段不同诗人的诗学观念及文本形态,我们可以区分,新诗“戏剧化”在整体层面上包含着诗人融合戏剧文类的“角色表演”“冲突性”“在场情境”几个文类因素,突破抒情诗的“诗人自我”“单纯抒情”“意象化”等常态,这是新诗发展中戏剧化探索的主要三层形态内涵。
本书这种概括基于不同阶段具体诗人的“戏剧化”诗观及相关文本依据。例如卞之琳对“非个人化”的追求,穆旦对“戏剧独白”的关注,张枣的“面具”创作动机自述,朱朱的“他者”情结自述,都体现了诗人化身戏剧“角色”的主体戏剧化意识。而袁可嘉“戏剧化”理论最核心最有效,且接通当代诗人诗学的,是他倡导新诗融合各种复杂甚至相反的情绪,达到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意味”,关注到反讽、悖论等现代修辞[39];在当代,西川提出诗人要面向“生活的矛盾”,诗歌要向包括“经验、矛盾、悖论、噩梦”的世界敞开[40],姜涛概括诗歌“由线性的美学趣味到对异质经验的包容”[41]的“综合”品质,张曙光从叶芝诗歌中悟出“往往是由矛盾的因素构成”[42],共同说明了现代汉语诗人对“冲突性”特质的重视。至于戏剧化手法,在卞之琳、孙文波、韩博等人的写作经验论述中亦有体现。从三层内涵来看,新诗“戏剧化”实为“化戏剧”,即诗人分别融合了戏剧的角色、矛盾、场景等美学理念或形态元素,从而区别于一般诗歌的“自我”直接出面、单纯情思表达以及纯粹的意象空间思维等典型范式。
整体考察不能脱离历时辨析。为什么“戏剧化”诗学观念或写作策略集中性地出现在新月诗人、九叶诗人和当代90年代以来的诗人这儿,各阶段对“戏剧化”探索的差异何在?寻踪一下,这三个时段诗人对语境的介入、对西方诗的相对谙熟、对形式的重视较一致,但“戏剧化”三层内涵侧重点及表现形态在三个阶段不一。第一阶段的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更注重言说主体的戏剧化和表现手法的戏剧化,体式探索自觉占据主导因素;第二阶段的穆旦、杜运燮等开始具有明显的冲突性经验情思和戏剧性修辞写作意识,同时也实践角色面具写作;到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诗人们的个体戏剧化观则涉及了三层内涵。
由此可以认为,从发生机制看,新诗“戏剧化”和“小说诗化”“小说戏剧化”相似,属于一种文类借鉴、文类融合的审美创作现象。关于“小说诗化”,方锡德、解志熙、赵园、杨联芬等学者从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的渊源、小说与诗的融合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沈从文、萧红、汪曾祺、废名等人的创作包含了“小说向诗的倾斜”,开创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形态[43]。常态小说的突出特征是鲜明的故事情节、明晰的活动环境、典型的人物性格,但“诗化”的小说则融合了诗的意象、意境、语言句式甚至韵律感,表现出“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44]。同样,一些研究者关于“小说戏剧化”的阐释也从文类融合的层面进行,认为“小说戏剧化”包括“戏剧理论对小说美学的影响,小说文本的戏剧性结构,人物、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戏剧性关系,小说家对戏剧的创作技巧的借鉴”[45]等等。“小说戏剧化”的著名实践者是英国现代小说家詹姆斯,他的戏剧化小说区别于一般的“叙述型”小说,以戏剧性场景的现场感和直观性,再现出“未经重新安排的生活”,让人物的一举一动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感受到“正在接触着真实”[46],从而实现他所追求的栩栩如生的真实传达效果。以这两者为参照,“诗歌戏剧化”也属于文类融合现象。
当然,虽同为文类融合现象,新诗“戏剧化”却不同于“小说诗化”。“小说诗化”最终的归依是“诗意”,小说家以此实现自然、自由心灵的率性表达,小说文本往往笼罩在诗性的情绪氛围之中,从而疏离了一般小说的“情节”“冲突”等鲜明要素。而现代汉语诗人的“戏剧化”,并非导向“戏剧”的激烈事件冲突,或在一个一定长度的动作过程中展现人物的命运,而是以“戏剧化”理念或因子扩容诗的表现空间和语言生成,目的仍是留在“诗”的园地,存有抒情性、主体性、想象性及语言的非陈述性等新诗的内在文类特征。从三层内涵来看,戏剧的角色、矛盾、场景等美学理念与要素只是帮助诗歌丰富、拓展文类表现范围和表现深度的策略、理念或途径。
因此,不能把新诗“戏剧化”理解为“诗剧”或者说把诗歌写成戏剧和叙事诗。严格地说,诗剧是以诗体对话写成的戏剧文本,它具有戏剧的情节冲突、故事结构、角色性格、舞台动作等完整的戏剧文类因素,因而成为独立并获得普遍“符码”认同的文学体裁。如郭沫若的《湘累》《孤竹君之二子》,海子的《太阳·七部诗》,皆以神话、历史中的角色或人物之间的矛盾故事为结构,展示了一定的外部冲突,具有动态发展的情节结构和隐含的戏剧性高潮等戏剧因素。而卞之琳、穆旦、陈东东等现代汉语诗人的“戏剧化”文本没有纯粹的外部动作或者显性的冲突性情节结构等特征,如穆旦的《神魔之争》,绝非一般意义的诗剧,而是诗人借助角色对白,传达自己对存在世界的思考,而且角色对白都是诗性隐喻。因此,新诗“戏剧化”不同于西方固有的“戏剧诗”[47]概念,探索者着意的仍是“诗”的抒发性和诗语言的多义特质。另外,“戏剧化”也不等于叙事诗中的“戏剧性”,叙事诗“围绕人的性格冲突及其命运的成长经历与‘故事’,以揭示人物关系并拓展叙事空间”[48],“戏剧化”则不指向故事。
“新诗戏剧化”也不同于“小说戏剧化”。戏剧对非叙事诗歌的融合、渗透不同于它对小说、史诗等叙事文类的渗透。小说、史诗和戏剧都包括鲜明的情节因素,因而互相之间具有自然的亲和关系。在小说、史诗等叙事文类中,场面描写、人物对话等戏剧化因素非常普遍,例如《荷马史诗》中两军对决的场景呈现。简单地说,把叙述主体抽离而去,让人物动作、语言直接呈现,小说就能实现“化戏剧”的“真实”效果。相比而言,新诗“戏剧化”侧重的是诗人由“自我”向其他“角色”生命意识的拓展、由单线情思向矛盾复杂经验的包容。至于“戏剧化场景”,诗人的本意也不像詹姆斯那样纯粹追求“戏剧化”的“真实”感,而是借助在场的效应达到“诗”的另一种意味,因此,诗人要成功地“化戏剧”,在呈现场景、对话因素的同时必须确保“诗”的言说方式,这就涉及一定的艺术难度和诗学抱负。
需注明的是,新诗发展当中的“戏剧化”和“散文化”“小说化”存在交叉关系。由于一些“戏剧化”文本的自由表现手法或情节性因素,“戏剧化”有时又和“散文化”或“小说化”等提法并置一处[49],不过三者之间仍有区别。根据前文可知,新诗“戏剧化”有自己的特定所指,而诗歌的“散文化”是相对“格律化”提出的,例如艾青把自己和戴望舒的文本,甚至所有无明显韵律特征的新诗都称为“散文化”[50]。另外,诗歌的“小说化”更倾向于指诗歌文本中隐含着情境、人物等事件性细节因素,但“戏剧化”不仅包含这一层面的意义,还指向“角色化”“冲突性”“在场性”或“呈现性”等艺术传达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