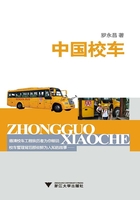
序
2011年,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录制时,我认识了来自浙江德清的罗永昌先生。这档节目探讨如何解决我国校车问题。当时,国内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德清的“长鼻子”校车引起全国广泛关注。浙江德清校车的经验可不可以复制到全国其他省市,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从那次节目录制后,我和罗先生一直未曾再次碰过面。直到最近,收到他给我发来的《中国校车》书稿——而不是《德清校车》。我可以理解罗先生的用意,他关注的不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德清方案”,而是“中国方案”。中国国情复杂,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相差很大,但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基本规律、原则应当是一致的。
我记得当初做节目时,罗先生针对校车经费来源的质疑,淡然地回应道,只要每位科级干部少配一辆车,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而且,实际运营的结果表明,校车的运营费用,还比给领导配司机的成本少得多。他的这番表述,让我坚定地相信,在中国,解决校车问题,缺的不是经费,而是决心和担当。《中国校车》一书,可以说是政府决心和担当的具体体现。
2012年,我国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舆论对于这一《条例》寄予厚望,希望其能让安全校车上路,为学生上学保驾护航。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一《条例》颁布之后,却出现了另外的景象:有的地方政府担心承担责任,只顾对校车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迟迟不给校车牌照,眼睁睁看着校车闲置,而孩子们却步行很远的路上学;还有的地方黑车死灰复燃。当地政府的目的不是解决校车问题,而是通过“消除校车”,来消除校车安全问题。当然,如果实行就近入学,所有学生步行都可解决上学问题,这可以不需要校车。但是,在我国乡村地区,即使就近入学,学生上学的路途也可能比较远,校车是不可缺少的,何况,还有不少地区根本就没有做到科学合理地布局学校。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政思维,这种思维之下,校车问题就将无解。德清解决校车问题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政府就主动承担解决校车的责任,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把校车的配备、运营纳入财政预算,交给专业的公交运营公司运营。这当然有“风险”——万一校车出事故,政府就要承担责任,但这种“风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而且,只要在校车配备、运营过程中,严加管理,完全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小,远比政府只负责监管,由各校自己配备校车、运营校车更安全、可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由学校自己购买校车,再招聘驾驶员,要求教师跟车保障安全,都超出了学校的责任范畴,这种模式不仅不可能保障校车安全,还分散了学校的办学精力。
也有人认为,校车属于福利范畴,若地方政府财政允许,可以给所有学校配校车,并统一运营校车,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就如当初,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保障义务教育投入,却指望通过收费,以及发动希望工程来建学校一样,是推卸政府办教育的责任。校车是学生流动的校舍,地方政府要像重视校舍建设一样,重视校车的安全。德清的校车能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这不是因为地方政府有钱,而在于地方政府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为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而更重要的是,我国要逐渐明确,解决校车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义务。如此,中国校车就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风景线。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