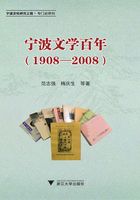
第三节 五四时期的小说
五四时期的宁波小说创作,是与当时整个新文学创作同步的。因史料所限,我们无法厘清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成员及其他社团的小说创作实绩,但从王鲁彦、王任叔等的创作来看,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领域小说创作的重要力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下,在鲁迅小说的影响下,他们以故乡风土人情为素材创作了多种作品,成为中国新文学初期乡土文学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一、朴素自然的浙东叙述者:王鲁彦的小说《柚子》等
王鲁彦(1901—1944),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后改为王忘我,笔名鲁彦。浙江宁波镇海大碶王隘村(现为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王隘村)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流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 。因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随父到上海做学徒。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蔡元培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自上海到北京大学旁听。其旁听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开始跟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1922年开始发表由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并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在《东方杂志》11号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秋夜》,并以“鲁彦”为笔名,以表达对鲁迅的仰慕之情,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因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随父到上海做学徒。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蔡元培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自上海到北京大学旁听。其旁听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并开始跟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1922年开始发表由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并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在《东方杂志》11号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秋夜》,并以“鲁彦”为笔名,以表达对鲁迅的仰慕之情,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王鲁彦文集》

王鲁彦
192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柚子》,1928年又出版了小说集《黄金》,从而奠定了自己“乡土文学的作家” 的文学史地位,成为中国现代乡土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927年任湖北武汉《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春至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1930年,鲁彦至福建厦门任《民众日报》副刊编辑。此后辗转在福建、上海、陕西等地大、中学任教。
的文学史地位,成为中国现代乡土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927年任湖北武汉《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春至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1930年,鲁彦至福建厦门任《民众日报》副刊编辑。此后辗转在福建、上海、陕西等地大、中学任教。
抗战爆发后,鲁彦积极投身于抗战洪流中,1938年在武汉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担任桂林分会主席。曾担任长沙《抗敌日报》副刊编辑,1942年在桂林与巴金、艾芜、张天翼等创办大型文学月刊《文艺杂志》,鲁彦担任主编。
1944年8月,正当壮年的鲁彦在贫病交困中病逝。
在20年的创作生涯中,鲁彦以其浙东人的刚毅倔强和执着,取得了丰硕而骄人的成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柚子》(1926)、《黄金》(1928)、《童年的悲哀》(1931)、《小小的心》(1933)、《屋顶下》(1934)、《雀鼠集》(1935)、《河边》(1937)、《伤兵旅馆》(1938)和《我们的喇叭》(1942)等;日记体小说《婴儿日记》(与夫人覃谷兰合著,1935);中篇小说《乡土》(1936);长篇小说《野火》(1937,又名《愤怒的乡村》,是鲁彦原计划描写浙江农民生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散文集《驴子和骡子》(1934)、《旅人的心》(1937)和《随踪琐记》(1940)等。并翻译出版了《犹太小说集》(1926)、《给海兰的童话》(1927,童话集,俄国马明·西尔皮雅克著)、《显克微支小说集》(1928,波兰显克微支著)、《花束》(1928,文艺论文集,法国查理斯·拉姆贝尔著)、《世界短篇小说集》(1928)、《失了影子的人》(1929,中篇小说,德国嘉米琐著)、《苦海》(1929,长篇小说,波兰先罗什伐斯基著)和《忏悔》(1931,长篇日记体小说,南斯拉夫米耳卡波嘉奇次著)等外国文学作品。
综观鲁彦的小说创作,正如杨义所说:“早期的王鲁彦是一个富有探索性的作家,他交换地使用过浪漫、象征、写实等多种创作方法,文无定宗,没有形成统一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他作为爱罗先珂的助手,深受爱罗先珂思想的影响。“鲁彦是一个赤心的大孩子,他闷的时节,不是弹琵琶,便是睡觉。半年以来,他替爱罗先珂做书记,受了爱罗君不少的影响。他的性格有些和爱罗先珂君相像。他们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他们最爱热烘烘的,他们永远是小孩子一般的心情。”
他作为爱罗先珂的助手,深受爱罗先珂思想的影响。“鲁彦是一个赤心的大孩子,他闷的时节,不是弹琵琶,便是睡觉。半年以来,他替爱罗先珂做书记,受了爱罗君不少的影响。他的性格有些和爱罗先珂君相像。他们都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他们最爱热烘烘的,他们永远是小孩子一般的心情。” 因此,在小说集《柚子》中的部分早期作品如《秋夜》《狗》《秋雨的诉苦》等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格调上,鲁彦直接受到了爱罗先珂的影响。“博大而又清浅的人道主义,愤懑而又天真的抒情风格,奇特而又带点幼稚的象征意象”
因此,在小说集《柚子》中的部分早期作品如《秋夜》《狗》《秋雨的诉苦》等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格调上,鲁彦直接受到了爱罗先珂的影响。“博大而又清浅的人道主义,愤懑而又天真的抒情风格,奇特而又带点幼稚的象征意象” ,这使他的作品在情感的表现上带有一定的直率和简捷,急于表达“所发见的人生的矛盾和悲哀”,其中也就难免“不无教训主义的色彩”,从而读来更像“能够动人的随笔”
,这使他的作品在情感的表现上带有一定的直率和简捷,急于表达“所发见的人生的矛盾和悲哀”,其中也就难免“不无教训主义的色彩”,从而读来更像“能够动人的随笔” 。同时,鲁彦师法鲁迅小说,却缺少了鲁迅小说的坚实与厚重。
。同时,鲁彦师法鲁迅小说,却缺少了鲁迅小说的坚实与厚重。
真正体现鲁彦小说“卓特的面目”的,是他从1925年开始推出的以《许是不至于吧》《菊英的出嫁》《黄金》等为代表的描写“自然和朴素” 的乡土写实小说。
的乡土写实小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20年代的乡土文学,是以鲁迅的乡土小说为滥觞,以侨寓于大都市的一批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小说流派。他们来自广袤的农村,向往着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但都市生活的隔膜和不稳定使他们产生的侨寓感、漂流感与精神世界的归属、情感的依恋等等,使他们对故乡产生了更深的眷恋。于是他们在开始创作时,就纷纷把目光投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农村,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他们的全新的思想与价值观,在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影响和启迪下,从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等角度重新审视自己深深眷恋的故乡农村,以写实的笔法,写出她的悲苦沉郁、她的闭塞保守与她的愚昧落后等等。
浙东,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江南小镇,浙东农村的人情世态、民风习俗,成为鲁彦乡土小说创作的丰富资源。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尽管鲁彦小说和鲁迅小说同样描写的是江南农民,但“活跃在他们作品中的那些愁眉苦脸的人物,却分别属于两个时代层面——在鲁迅作品中那些依照传统方式愚钝而麻木地生活着的乡下人,到了鲁彦笔下,则平添了不少商业气息” 。这种分析无疑是准确的。
。这种分析无疑是准确的。
在内容上,鲁彦小说以镇海乡镇农村为主要叙述对象。一方面高扬五四启蒙主义大旗,以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新的观念来重新审视故乡风情,写出她的陈旧落后与破败萧条,力图引起读者的深刻反思——《岔路》中的驱妖与械斗,《河边》中病体奄奄的明达婆婆宁愿到关帝庙去求神而不愿进医院,等等。这其中《菊英的出嫁》无疑是最为人所关注的。《菊英的出嫁》描绘了浙东农村的“冥婚”陋习。菊英七八岁时便已经夭折死去,十年后,一起出生的伙伴们都已经成家生子,安享天伦之乐。于是菊英的母亲想到死去的菊英。她开始跋山涉水地张罗菊英的婚事,为她寻找到一个门当户对年龄相当的同在阴间的“丈夫”。然后开始像一门正常人的正式婚姻一样,请人说媒,合八字,然后大肆置办婚礼,极尽铺排。作者极为细致认真地叙述着菊英母亲及相关人们为这场婚礼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和绝不亚于常人婚礼的隆重热闹。这一方面写出菊英母亲对死去的女儿的深深的思念与关爱,向我们叙述着母亲内心的情感缺失造成的深沉的悲哀,从而使作品成为一曲深沉的母爱挽歌。但同时更令人深思的是,面对这隆重而热闹的一场近乎闹剧的婚礼,我们不能不为这古老大地上不断上演的自古相传的陈风陋俗而生发感慨!
鲁彦小说的另一方面,则真实地记录了随着半殖民地程度加深,在外来商品经济对乡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巨大冲击下,几千年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价值体系逐渐被金钱至上的商品经济体系所取代。外来商业文化将它本身携带的阴暗面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落后面结合在一起,原本农业社会乡民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裂了,很多人拜金主义思想严重,一切以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的标准——《黄金》叙述了发生在浙东一个叫陈四桥的小镇上的世态炎凉。主人公如史伯伯本是家境“安安稳稳的”殷实的人家,儿子在外谋事,并按月汇款到家。在陈四桥这个看似民风淳厚古朴的乡村世界里,如史伯伯享有着乡邻们的尊重,邻里之间关系也无比融洽。然而年关将近,如史伯伯儿子的汇款却不知何故迟迟不能汇来,如史伯伯心急如焚,每日翘首期待,而其处境也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乡邻们开始纷纷猜测他的儿子一定是在外闯祸出了什么事,无钱寄回家了。于是,关于如史伯伯破产的流言迅速蔓延开来,人们对他家的态度立即改变:上门行乞的乞丐突然变得盛气凌人,满含鄙夷起来;债主们纷纷提前上门索款,并动手搜拿东西;如史伯伯的女儿在学校无端受到欺侮,连他家的狗也被人打伤。出席邻里婚宴,如史伯伯也不再享有以往的尊重,虽白发苍苍却屈居末席。家里被盗也不敢报案,怕人们说他假装失窃,不想还债。仅仅因为一个毫无根据的臆测,昔日备受尊重的如史伯伯便如丧家之犬,世人以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市侩手段,给予如史伯伯一家难以承担的羞辱。鲁彦以他对故乡人情世故的谙熟,用他的敏锐的感觉去描写,通过一种戏剧性情景的设置,将浙东小镇金钱灵光笼罩下的炎凉世态揭示殆尽。
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小说的主要代表,正如杨义所说,鲁彦的小说朴实自然,细密含蓄,“醇厚中带点悲苦,平实中回荡着几分抒情,落笔略显沉闷,缺乏令人啼笑的艺术刺激性,却不乏令人心情沉重的艺术感染力……他的风格属于乡土写实小说的正宗” 。
。
这种乡土写实小说的正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浙东滨海水乡环境、民众行事习惯和传袭信仰的描写,使鲁彦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上述《菊英的出嫁》反映了古老相传的浙东(乃至全国)农村的“冥婚”习俗,《岔路》讲述的两个村庄抬关帝爷出巡驱除瘟神引起的械斗,《小小的心》记载拐卖儿童而世人却习以为常的野蛮村俗,《鼠牙》写用“老鼠嫁女儿”的方法将老鼠赶到邻家的邻里之争……这样的风俗画在鲁彦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小说涉及的地理名称,同样充满滨海乡村的特点,如陈四桥、朱家桥、北碶等。小说中的语言也充满浙东气息。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多是被地方政权、古老相传的落后习俗和外来商业文明所压迫、损害的底层民众。
宁波方言在小说中的运用,是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又一特色。例如:
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前天亦已摆放得妥帖,各种事情都有人来代我排布。
——《许是不至于吧》
“排布”,安排的意思。
这二十万的家产总要弄得一秃精光的了!
——《许是不至于吧》
“一秃精光”意为一点都不剩。
全屋如要崩倒似的噪闹,清静连在夜深也不敢来窥视了。
——《许是不至于吧》
“噪闹”意为把房子都要吵倒的吵闹。
吉期前一天晚上,官筵开始了。这一餐叫作“杀猪饭”,因为第二日五更敬神的猪羊须在那晚杀好。
——《许是不至于吧》
“杀猪饭”那晚要杀猪,那天的晚饭叫杀猪饭。
“阿品,口琴起驼来吹吹好勿?”
——《小小的心》
“起驼来吹吹好勿”意为去拿来吹吹好不好。
时时刻刻倚傍着自己的娘,“阿姆阿姆”的喊。
——《菊英出嫁》
宁波人叫妈妈为“阿姆”。
最先走过的是两个送嫂。
——《菊英出嫁》
送嫂专于婚丧时服侍女客,或平日与妇人绞面。
后面一顶“鼓阁”两杠纸铺陈。
——《菊英出嫁》
鼓阁系一种轿子形式,内置乐器数种,以一人司之,与轿后数人之乐相和。
她六岁时自己学磨纸,七岁绣花,学做“小脚娘子”的衣裤。
——《菊英出嫁》
磨纸,即磨锡箔。“小脚娘子”系女孩以各色布自做的女玩偶,以其小脚,故名。
方言,不仅以其特殊的表现力增添了小说的乡土气息,也使小说中的人物特征更加生动形象。方言土语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又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王鲁彦的小说里没有运用一些方言土语,他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就不会如此生动形象。
鲁彦短暂的一生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奋起斗争,挣扎于贫病加劫难之中的真实写照。从其一生的著、译、为人和文学活动看,鲁彦不仅是一位忠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而且还是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忠诚斗士。而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更成为一位伟大的抗战文艺的前线勇士,其在世的最后五年大多在广西桂林,除文学创作外,主要参加了作为抗战文化前哨的桂林的文化活动,如参与文协桂林分会的筹建和各种抗日文化活动,历任文协常务理事、理事;特别是抱病坚持筹办并主编了大型文艺月刊《文艺杂志》,直到肺结核病重不治逝世。
二、写实抒情并重:巴人的小说
巴人(1901—1972),浙江宁波奉化(现为宁波市奉化区)人,谱名王运镗,字任叔,笔名巴人。他13岁参加全县小学统考,作文名列前茅。1923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1924年10月任《四明日报》编辑,主编副刊《文学》。1925年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的重视。巴人的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小说的内容,从农村到城市,从监狱到官府,三教九流,五光十色,凡是巴人经历过的,在小说中都一一出现,形成了题材广泛、人物庞杂、视野开阔、产量丰富的创作特色,总括巴人小说的创作风格,就是写实与抒情的色彩比较浓重。

巴人(王任叔)
巴人早期的小说主要收在1927年出版的《监狱》和1928年出版的《破屋》中。
作为浙东山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巴人爱憎分明,正直倔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对伪文人、地痞流氓、剥削者、故作学问之徒和假正人君子都痛恨之极,并给予无情的嘲讽,而对弱小者、贫雇农等弱势群体他又十分同情。因此他的小说形成两种情调:冷嘲热讽式和爱恨交加式。那些描写城市无赖、农村剥削者的小说,多是语含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反映城市无产者或农村雇农的小说,则是爱恨交加,恨铁不成钢。巴人曾说:“现实主义者的路,不仅在作品上着重现实主义作风的创造,而首先应着于生活经验与人格之现实主义的作风创造。”巴人的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他创作的时代感,由是产生了他的乡土小说、都市小说和讽刺小说。
巴人的乡土小说主要是侧重于表现生活在浙东山区的一群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在小说中他塑造了奴性型、反抗型和不满型等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并且揭露地主、乡长、县老爷等农村中基层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和凶残本质,如《灾》《血手》《族长的悲哀》《乡长先生》《勘灾》等一系列小说。巴人不像有些乡土作家喜欢以极为抒情的笔调描写故乡生活的甜蜜与温馨,他执着地抒写故乡极其贫穷的农民们的苦难和不幸,借此来抨击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时代和社会——从最初的小说《河豚子》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作基调。巴人笔下的故乡人都是极其不幸的,他用理性的眼光描写这些人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不忘向读者们揭示酿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在《雄猫头的死》中,“雄猫头”是一个上无父母旁无兄弟的木讷勤劳的农民,他终日食不果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讨上老婆,却在官兵来“剿匪”的时候无辜被当成眼线割了头。“雄猫头”的死抨击了军阀草菅人命的恶行。《运秧驼背》中的“运秧驼背”是个雇工,他出佣的工钱特别低,只因为饭量大,富户很少雇他,而雇他的人又克扣他的工钱,饿了他就嚼些草叶或在破烂的三圣殿昏睡。尽管贫困,但是他有骨气,从不占别人的便宜,然而在最后他还是被乡绅诬陷偷别人的钱,吃了一年的官司,沦落为乞丐。他的命运揭示了社会对于下层人的不公平。《白眼老八》中辛勤一世却贫困一生的白眼老八,对农民有诚挚的爱,却和自己的乡绅哥哥老对着干,最后在大雪之夜孤独地死去,控诉了黑暗社会罪恶的剥削。在《追剿》中,在黑暗时代中挣扎的乡土社会的人们有的在官兵的剿匪中被无辜打死,有的在追剿中被割下头作为领赏的凭证。在《灾》中,主角是一群在财主贪婪地砍伐山林后的暴雨中被活埋在坍塌的山石下的农民。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破屋下的人们”的生存状况,悲惨和不幸是巴人小说表达的主题。巴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分析农民的现实生活,理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所以1928年文坛以“民间小说家”来称呼他。他的可贵处在于他不局限于同情农民的立场,而是站在历史运动的潮头上以逐渐显明的阶级意识分析、认识、把握农民。
翻开巴人的作品,在描写乡土那块踏实的土地上,我们认识的不仅仅是生活在浙东地区的那些贫困的农民们,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同时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浙东山光水色、乡规俚俗和生活风尚。巴人的小说能让我们了解浙东地区的各种生活,诸如械斗、诉讼、上坟、求神、祭祖、开贺,如何捐监生、买功名、奉祖庙、聚学田、请龙王、出稻会,如何吃大户、打龙灯,乃至充满野性的聚赌、虐杀、抢亲、野合……在官场、洋场、村场、文场的众生交错中,巴人把握的是那个时代的命脉,揭示出的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互中的浙东乡村人民的人生百态。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巴人一直在城市生活,这个时期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小说的描写对象也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巴人的都市小说,大都从微观角度反映生活,即通过生活的一角反映都市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生活。在巴人的都市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主要有三类——城市的上层人物、下层被统治人物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城市游离者。不同于前期乡土小说的人物塑造大都是在对立中来体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市小说中的上层人和下层人在巴人的笔下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大部分是通过直接的描写来显示人物的特点,如《自杀》中描写软弱、顺从的勤生木匠的自杀,《仿佛》中的工人大喜子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悲惨遭遇,《负责人》中的王子霞以口头上的忙和行动上的不忙来欺骗别人的丑陋行径,《为人在世》中阿七的见风使舵和极端自私的“秤杆主义”哲学。总的来说,巴人的小说都侧重于揭露现实,因此,巴人的都市小说和前期的乡土小说在主题的表现上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巴人的有些小说也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大波动、工人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展现了较为广阔的历史画面,如《六横岛》和《女工秋菊》,但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没有恢宏的框架,不是从整体上反映激荡的时代风云,而只是从一个片段或一个角落来描写都市。所以,在巴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更能真实地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生活和历史风貌。
巴人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情异常的广阔,小说只是巴人文学作品风景画中的一隅。巴人可以说是个文学全才,他对文学的投入范围与气魄,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项背。他的诗歌和杂文在众多的文学大家中也毫不逊色。可以说,他是唱“挽歌”的诗人,他是真切的“民间小说家”,他是忠诚的革命者,这位铁骨铮铮的浙东硬汉用他的一生谱写着浙东文学的地图。